我的565
在那樣的年紀,迎著陽光像塗防曬乳,流著汗水像噴體香膏。重低音舞曲是腦中的口香糖,時常咀嚼,要反覆攤平刻在腦中皺褶的試卷遺跡。那是在騷動不安的年齡,一首特別的樂曲。
初見面是在電視機螢幕前。那個年代,MV盛行,突然滿溢出來的頻道,沒日沒夜播放著情歌裡的男歡女愛、你怨我恨,不是愛別離,就是求不得,差別有時只是角色與情節。換句話說,說的差不多。
但我根本不會料到有這麼一幕。電視螢幕裡,雷聲乍響,小提琴穿越堤岸,橫過野地,直飛到女孩的手中。在水一方,緩緩奏出開頭的下行音階。在逐漸堆疊的和弦音中,海風吹拂過她的裙擺,此時卻令人覺得烏雲壓頂,山雨欲來。突然,一個音斷,感覺話還沒說完,接著劈頭便是一陣疾風驟雨,雨腳細密,密密麻麻的高音低音競逐傾軋,讓人來不及拿休止符壓驚。中間雨勢稍緩,但風聲凌厲,雙簧管吹出一段模仿旋律,上下搖曳。霎時雨勢又起,薩克斯風插縫灑出齊整琶音,引出小提琴接手回應。鏡頭忽遠忽近,旋轉不定,樂聲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此時只有貝斯黏著鼓聲,在雨中一直踩著規律的舞步,催促耳膜快點跟上。
樂聲稍歇。撥雲見日後,主角衣著一改,身穿無袖緊身半截露臍裝,緊身熱褲搭及膝長靴,在荒野中拉起旋律如穿透雲層的光束。只見樂手一下在荒地間奔跑,恣意的黑髮如馬頸鬃毛飄飄,轉眼又立白巖前,扭動蠻腰作嬌蛇舞妖嬈。主角或跑或走,或站或蹲,旋律也靈動,樂句像是由光束雕刻打磨的雲朵,十六分音符層層推進,如雲翻,如浪湧。旋律在上,高音入雲,旋律在下,低音伴浪。明明每一片浪花和雲朵那麼的相似,卻又在節奏變化下,片片朵朵不同。然後身體不由自主,隨著律動搖頭晃腦。
接下來樂音又變。高音部三十二分音符上下快速搖動,像蜂鳥搧翅。低音部拋出疑問,接下來的和弦還沒給出答案,高音部又開始飆起狂風,旋律便在一長串迅捷的你答我應中慢慢迎來尾聲,狂風撼雨樹,掉落滿地的,不是輕盈的雨珠,而是清脆的驚嘆號。樂手離弓,一塵不染,乘音遠去。
如此狂野,如此豪放,如此瘋狂,又如此令人著迷!野馬迎著狂風暴雨疾奔而來,在燦燦陽光中穿雲破浪而去,一騎絕塵,也當如是!
我開始搜尋有關這首樂曲的種種。原來,樂手的名字叫陳美,是位才華洋溢的小提琴家,而她所拉奏的曲子,是改編自巴赫的管風琴曲〈d小調觸技曲與賦格〉,在巴赫作品目錄(BWV)裡編號是565。
後來在聆聽樂曲的過程,發現又是另一番天地。MV的長度,有點像是精華版,實際的樂曲長度遠遠不止於此,裡頭有更多的細節,帶給我更多不同的體驗。小提琴改編版,把旋律巧妙分給不同樂器表現,加上節奏動感強烈,給人目不暇給、繽紛奔放的感覺。至於管風琴的版本,音色的變化無法那麼明顯,因此聆聽時要辨認旋律和段落,更需要專注。
我帶著許多疑惑,開始在學校圖書館的曲目解說裡搜尋蛛絲馬跡。但是厚厚一本書裡,單一曲目的說明只有寥寥數語,無法滿足我。我開始接觸古典樂,參加學校樂團,學習音樂,練習演奏。我想弄清楚,為何這些音符,為何是這樣的排列方式,能將我纏裹虜獲,讓人手舞足蹈、念念不忘?
有次,在學校樂團認識的好友找我一起到文化中心的地下室,他說那裡有許多樂譜。到了之後才發現,哇,原來那裡有間音樂圖書室,裡面有許多書、光碟,還有許多樂譜。進到書櫃前,我拉開櫃上的玻璃窗,在一整排黃色封皮的樂譜裡,找到巴赫的名字。我越過許多清唱劇(多年後我才知道裡頭藏著珍寶珠玉),往管風琴作品的分冊找去,終於找到了這首曲子的譜。我把冊子拿到影印機,心滿意足把它印下來保存。記得那天,好友和我另外還印了許多的譜,但最後我興奮對他說:「今天我最高興的,就是印到這一首的譜。值了!」
拿到譜之後,細細端詳,發現許許多多的音符上上下下,好似波浪。三十二分音符的律動,也像鳥兒奮力展翅留下的弧線。更特別的是,這些音符,還能造成狂風驟雨的體驗。於是我尋思,把譜上的白紙黑字,和記憶中的音響效果,拼湊在一起。
後來,對音樂的技術層面了解更多,慢慢才知道,那些引我把點頭當節拍器的,原來是密不透風的旋律模進。那些我聽到互相競逐的旋律,其實是主題與答題在賦格的泳池裡你來我往,互興波浪。而那些令人屏氣凝神,或懸懸不定的瞬間,其實是刻意安排的和絃行進,用漸慢或延長刻在耳膜上的印記。
這樣一首動聽特殊的曲子,是如何來到人世間,讓眾人所知呢?
放眼望去,有許多人也喜愛這首曲子。原來這首曲子大有來頭。一八三○年代,孟德爾頌協助出版了巴赫的管風琴曲集,其中便有這首曲子。後來這首曲子也在李斯特的手下風馳電掣,然後李斯特的門生陶西格,以及另一位鋼琴家布梭尼也各自將之改編成鋼琴版。
到了二十世紀,改編的作品更是五花八門。例如,指揮家史托考夫斯基有管弦樂改編版,此版本也因著出現在迪士尼的影片《幻想曲》中而進一步廣為人知。除此之外,還有長笛版、爵士版、搖滾版等等。此曲還現身在其他電影裡,例如《化身博士》和《歌劇魅影》,更進一步推波助瀾,使得這首曲子在大眾文化裡穩占一席之地,現今在許多不同的改編作品裡皆可見其蹤影。
不過,大約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許多學者提出質疑,認為這首曲子並非巴赫的作品。有學者認為,這首曲子的語法風格,和巴赫的其他管風琴作品很不像,懷疑是其他人的作品,只是在傳抄和保存的過程中,出現了張冠李戴的情形。有學者鑽研巴赫的學生德雷策爾的一首嬉遊曲,檢視其中的結構和寫作手法,發現與BWV 565的特點十分類似,因此猜測此曲或為德雷策爾所作。
而不僅作者的地位受到質疑,有些學者還認為,從樂句結構來看,這首曲子原本是寫給小提琴的作品,理由是譜間充斥經常出現在小提琴演奏上的交替奏法,後來才採寫成管風琴譜。有些學者說,可能原本是寫給魯特琴、大鍵琴等等。
另一方面,有別的學者,如知名的巴赫專家沃爾夫則主張,這首曲子是屬於巴赫早期的作品,所以自然有很多和後期作品不同之處。再加上可能受限於當時某些管風琴的結構與性能,才使得這首曲子的某些樂句,迥然不同。也有學者支持此說法,並舉例說明,其實這首曲子的特殊語彙,也可見於巴赫的其餘作品,如BWV 572。儘管理論各有千秋,但對於作者議題,至今仍莫衷一是。這樣名滿天下的一首樂曲,作者竟然成了一個謎,人人有猜測,無人能定論。
而從樂曲的某些細節,學者還考證出不同大師留下的印記。巴赫的前輩音樂家帕海貝爾,他有一首〈D大調卡農〉,現今家喻戶曉。有學者在他的〈d 小調幻想曲〉(P.124)中,發現有個樂句,轉化成為BWV 565賦格主題的一部分,也套用在之後的賦格發展裡。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將布克斯特胡德的〈d小調觸技曲〉(BuxWV 155)與BWV 565對舉,發現許多的相似處,如自由幻想風格,以及腳鍵盤上的持續低音等等。而巴赫年輕時曾長途跋涉去聆聽布克斯特胡德的演奏,據說從那之後,他的管風琴演奏大為不同。若這首曲子是巴赫所寫,那麼從當中看到不同大師的靈光匯聚,對海納百川的他似乎也是順理成章。
不論真實作者到底是誰,當初坐在管風琴座上的那位琴師,在彈奏這首曲子的時候,或許也是大開大闔,少年得意?而這巧妙樂思,竟從巴洛克時期,奔騰數百年到現代人的耳中,也成為我青少年時期難忘的回憶。
是啊,那時的人生,總想把自己當成野馬,在狂風暴雨中狂奔。在髮型上雕琢,在衣著上費心。總是想在安分念書考好成績外,在其他領域開疆闢土,馳騁一番。總是想讓人眼目一亮,出聲欽羨,讓人順道忽視我課業的表現。但名駒良馬雖有,但總歸是別人家的。
記得有一次,那位約我去印譜的好朋友,找我一起騎機車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原來他要去找一個已經沒有同住的至親。他和她很久沒有見面了,他很想念她。我們約了一天,偷騎機車,一路過橋越溪,穿過鄉鎮市區,經過矮房高樓,南下到很遠的地方。到了之後,她親切招呼我們,我看見朋友臉上欣慰滿足的表情。但這已是另一個他只能拜訪,卻待不進去的家庭。
那天下午回程的路上,南部的陽光很熱情。但我記得有一個路段,我們經過樹蔭下,密密麻麻的樹葉用微風,把亮燦燦的陽光篩成一顆一顆溫暖的細鑽,像賦格此起彼落,像海潮前仆後繼。啊,原來生活也可以有這麼溫柔的時刻,在言語之外,在沉默之中。
原來,生活中有更多的謎。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當初相愛的兩個人,最後要互相傷害。為什麼有些努力,看不到盡頭。為什麼有時連問為什麼都懶了,只能說算了、認了。
原來,在音樂裡的狂風暴雨,已是生命中的溫柔。在音樂裡,不和諧音往往只是暫存,如果作曲家願意,通常會用巧手喚出旋律或和弦,把衝突解決。在音樂裡,把悲傷說出來,會得到撫慰。把心碎交出去,會得到同理。把不堪攤開來,會收穫擁抱。把眼淚灌進去,會淬鍊出平靜。
啊,那時年少輕狂,我享受那些日子,音符在細胞的記憶上恣意紋身,有時狂風驟雨如草書狂放,有時絲絲斜陽如小楷端麗。如今只剩古道西風瘦馬,馬蹄闌珊,踩碎泥濘裡的殘夢。啊,如果我們還有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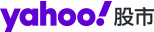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