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處求醫卻不斷被踢皮球,是俗稱「公主病」的纖維肌痛症患者最真實的寫照

文、圖:梅緣緣
四處求醫,卻不斷遭到「踢皮球」。難以獲得適切的治療與診斷,是纖維肌痛症患者在求醫時,最真實的寫照。俗稱「公主病」的纖維肌痛症,不同於一般受傷感染,患者多主訴自己全身上下都在痛,卻又無法找到身體在病理上的變化。
「你好······」小如(化名)微弱的聲音從話筒另一端傳來,患有纖維肌痛症的她,聲音微弱到時不時被她附近便利商店高頻叮咚聲蓋過。生活天天圍繞纖維肌痛症打轉,小如更因為長期吃藥,兩年胖了近30公斤,成日腰酸背痛,連要正常走路都很困難。
一天服用七八顆藥的日子已成日常。利瑞卡、千憂解、抗發炎和止痛配水服用,在那些痛度特別高的日子裡,有時更會多吞幾顆止痛藥試圖降低神經敏感度,「多吃幾顆,至少可以比較有舒緩的效果。」小如說完輕輕嘆了口氣。
無法取得鴉片類止痛藥、又痛到無法忍受時,另一款藥物安保舒痛錠成了纖維肌痛患者鎮痛的佳選。
當與疼痛為伍成為常態:患者的日常
「沒吃藥的時候,疼痛會有八九分,常常想死。」小如確診為纖維肌痛症已超過六年時間,每天睜眼後的生活,對她來說都是場硬仗。20幾歲墜入憂鬱症的深淵,小如怎麼也料想不到除了心靈上的折磨,還意外抽中命運,自44歲開始,整個人心理連同生理一併遭纖維肌痛症吞沒。
受全身性疼痛所佔滿的生活,也讓她無法外出工作,不得不長時間靜養。「只有躺著才比較舒服」,她形容這種疼痛,有時只是某個部位會出現嚴重的刺麻感,有時則像有電流不斷流過整個身體。
患者尤琦雯還沒發病前是名護理師,約莫在30歲時身體逐漸出現「這裡痛,那裡痛」的狀況。除症狀不勝其擾外,一次意外又不小心摔傷脊椎,也使得經常需要輪班的她,無法再勝任護理師繁重的工作,被迫從護理領域黯然退場。病況也隨著年紀的增加而惡化,「到後來需要鴉片類止痛藥才能緩解,」尤琦雯緩緩地說。
「得到診斷怎麼這麼難!」頻頻受挫的就診經驗
卓新復健科醫師卓彥廷指出,纖維肌痛症迄今仍無法找到確切病因,也沒有標準化的方法實際證實纖維肌痛症的診斷。只能根據患者主訴搭配理學檢查,可能可以發現病患疼痛敏感度或發炎指數上升,但無法看出明顯病理上的證據。因此,要在臨床診斷是否患有纖維肌痛症,一般採行排除法,刪去可能出現相同症狀的甲狀腺、免疫系統疾病或感染等。不過在試圖排除各種疾病的可能性時,也變相拉長了患者痛苦,也加深他們內心對未知的恐懼。
「跑了很多間醫院,林口長庚、台大、台中榮總啊。看了各科醫生,也做了各種檢查,想得到的幾乎都做了。」這是受訪的纖維肌痛患者們一致的就醫過程,也因為社會對於纖維肌痛症了解不多,所以纖維肌痛患者很少是在首次看診時就成功獲得診斷。他們的求醫過程多半既曲折、耗時又須花費大筆金錢,而這也是在病痛之外的另一種磨難。
對此卓彥廷則解釋,要判斷求診者是否患有纖維肌痛症,診斷的基礎條件中,患者的疼痛範圍,須同時涵蓋身體兩側與腰部上下18區域內,超過11處有明顯壓痛點;疼痛也必須持續存在三個月以上,才有機會確診。
不過患者除身體疼痛以外,也經常合併各式自主神經及憂鬱、焦慮等共病,遊走各大醫院科別,卻還是無法知道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纖維肌痛症壓痛點
纖維肌痛症患者的診斷,多憑18個壓痛點中有11處以上壓痛,作為初步判斷標準。
因此,美國風濕病學會於2010年,提出了另一基於症狀的替代診斷方式,如「廣泛性疼痛指數(WPI)」與「症狀嚴重度量表(SS)」,其中症狀嚴重度包含的項目就有,疲勞、睡眠障礙、身體不適等。卓彥庭說,若廣泛性疼痛指數大於7且症狀嚴重度量表大於5,疼痛超過3個月,沒有其他可以解釋該疼痛的疾病時,便可符合診斷標準。
纖維肌痛症加重因子
纖維肌痛症無論是在罹病前或罹病後,皆與個人身心狀態息息相關,其中情緒緊張將導致患者對於疼痛更為敏感。
觸發纖維肌痛症的前三大原因
雖研究結果顯示纖維肌痛症多為心理因素觸發,但生理因素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台大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孫維仁,診療過許多纖維肌痛症的個案,十分了解患者正面對著什麼樣的生活衝擊。孫維仁說,某日一名企業主出現在他的門診,一坐下就開始抱怨全身疼痛難耐。
經詳細的問診和症狀檢驗,孫維仁發現她其實罹患的是纖維肌痛症的當下,如釋重負的企業主頓時整個人泣不成聲。「原來自己的疼痛,是有原因的,」這幾年來她身心所受的苦難與折磨,現在終於有人懂了。
孫維仁表示,許多患者雖多年後仍未完全康復,但至少他們都陸續找到了方法,來面對無所不在的疼痛。有的病患會毅然決然地離開職場、轉換工作環境或找一份比較輕鬆的工作,只要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就能降低身體出現劇烈疼痛的頻率。
不過孫維仁也坦言,有辦法迅速提出離職的人在經濟上,多半較為寬裕;有些患者因為種種因素,無法脫離原本的生活型態。「但這樣在和疼痛和平共存上,就顯得較為艱難。」孫維仁的語氣略顯無奈,卻也道出部分纖維肌肌痛症患者艱困的處境。
失控的疼痛漩渦 患者生心理的變奏
幸好,一個月總會有那麼一兩天,難耐的疼痛會和小如暫別。那段時間重拾回一些體力的她,除了還是會預防性地服用止痛藥外,也會選擇去附近的菜市場晃一晃,當成小小的運動。可是小如認為,雖然短暫遠離疼痛,但身體發炎指數仍居高不下,很容易又掉回「這邊痛,那邊痛」的狀態。
小如也與憂鬱共處了30多年,經常懷疑自己的纖維肌痛症是受憂鬱症所觸發,因一系列的症狀都在情緒逐漸潰堤時紛紛冒出。現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的她,以略顯抽離的方式,描述著自己到傍晚的身心是如何完全走樣的。「情緒低到不能再低,變得無比脆弱,好像一碰就碎」她這樣子形容;挟帶著的死亡念頭過於凶猛,在既無助又瀕臨崩潰的情況下,多數時間只能靠不斷地自殘,化解想就這樣一走了之的衝動。
除了纖維肌痛症,也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蘇西認為,從小面臨家族成員性騷擾所產生的創傷,再加上先天動不動就生病的孱弱體質,讓她懷疑纖維肌痛症在她小的時候早就已經如影隨形。
「就像火山一樣,爆發過一次後就有源源不絕的溫泉,而這溫泉對纖維肌痛症患者來說,指的就是『疼痛』。」孫維仁指出,纖維肌痛症患者的發病原因,有時是身體受到意外傷害,有時則是幼年時期曾經歷過的心理創傷,種種情況都有可能誘發纖維肌痛症產生。
會產生這一連串的疼痛,是因為「你的身體太愛你了。」孫維仁瞇著眼睛說,疼痛就像汽車的倒車雷達,在車子快要碰到後面的物體就會不斷發出警告。「但纖維肌痛症就是(你的身體)變得太敏感、失靈了。」這就是原本的保護機制失去作用,反而產生大量誤報,很難不把人逼瘋。
面對這些無所不在又各個身心俱疲的病患,孫維仁也必須承認,在一般怕被貼上想佔便宜,或不想做事標籤的情況下,要患者跟身旁親友、同事坦白自己的狀況,難度其實非常高。
孫維仁認為,「發作頻率」與「疼痛的不可見性」是很多纖維肌痛症患者一直居處暗處,不願發聲的主要原因。即便告訴患者如果不舒服可以說,久而久之也不能確保對方是否會感到厭煩。患者自行評估或嘗試幾次失敗後,可能就會選擇乾脆不講。
同時身為「台灣人的纖維肌痛症」社團駐版醫師的孫維仁,診治患者外,也常在社團內分享纖維肌痛症相關資訊。
當適應症用藥無法讓患者脫離失能
「利瑞卡(Lyrica)」是多數疼痛科針對緩和纖維肌痛症疼痛的首選藥物。據台北榮總疼痛控制科止痛藥物說明書,服用利瑞卡的可能副作用包含:頭暈、嗜睡、口乾、水腫、視力模糊、體重增加及注意力下降等,但對控制疼痛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與選擇服用利瑞卡止痛的纖維肌痛者患者相反,蘇西在被問到醫生是否有開立「利瑞卡」或「千憂解」時,輕嘆了一口氣說:「疼痛科藥物吃了會長時間昏睡,我需要賺錢,所以沒辦法吃這些藥。」同為患者,林瑋也表示她在確診罹患纖維肌痛症後嘗試過利瑞卡,「但吃完會全身癱軟,完全使不上力,連起床也要別人公主抱。」她無奈地說,只好另尋其他解決方法。
嘗試過西醫治療效果都有限的情況下,林瑋和許多無法或不希望使用藥物的患者,面對疼痛通常會決定改求助於物理治療。另外的患者,可能會選擇其他如局部注射葡萄糖、順勢療法、維持清淡飲食等方法來控制。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心靈呢?
憶起當初求醫的過程,小如略顯激動地表示:「我們的痛,是無時無刻的。希望業障還一還之後就走。」語畢,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雖然小如強調,自己算是病友裡面比較幸運的,但面對像家人質疑和不解的眼光仍備感壓力。小如說,親友不一定每個人都會認同這個疾病,可能還會覺得不能出去工作,就是在為自己的懶惰找藉口;像是自己的媽媽就會覺得,老一輩人從小做到大也就這樣撐過來了,為什麼自己就不行。
蘇西和小如一樣,周邊親友的眼裡容不下纖維肌痛症的存在,認為無法觀察到的疼痛,只是在為自己的懶惰和不負責找藉口。「從小症狀多到不知道該怎麼辦,家人會覺得我是在無病呻吟。」最親近的人卻最難諒解,雖然讓蘇西倍感挫折,但努力調適好心情狀態,才能做好與疾病長期抗戰的準備。
現在是幼稚園助教的蘇西,在美勞教學的備課上,有時也會面臨一番苦戰。像是拿著剪刀的手想剪出一個好的半圓,卻發現手指跟手腕一出力就很痛,最後剪出來的半圓看起來像被狗啃過。然而,因擔憂除須向他人解釋外,還可能遭他人投以異樣眼光,所以即使在工作上因纖維肌痛症而出現困難,蘇西還是忍著痛把工作做完。
讓無形的纖維肌痛被看見
「纖維肌痛症無法列入重大傷病,所以只能用憂鬱症的部分來申請。」尤琦雯認為,要不是因為纖維肌痛症纏身,個性開朗的她根本就不會有憂鬱症。
受疾病和共病纏身所伴隨而來的經濟負擔,也常壓得患者們喘不過氣。身體各部位輪流拉警報,讓患者進出醫院像逛市場一樣頻繁,每月也至少要支出超過四五千在掛號費和醫藥費上;有些病患運氣比較差,看診的醫師對纖維肌痛症沒有太多概念,就可能要花更久的時間、更多的錢,試圖釐清自己到底罹患了哪種疾病。
「我跟你說,我這樣的狀況沒有辦法辦保險。」她的語氣有些焦躁無奈,因為保險內規拒保纖維肌痛症,即便有保險業務來推銷,也只能笑笑地跟他說不是不願意保,而是沒辦法納保。還好尤琦雯的家人對她罹患的纖維肌痛症較為諒解,沒有增加尤琦雯太多的心理壓力,「啊,但自己的開銷還是會自己付。」她補充。
與尤琦雯比起來,因為無法獲得家人的諒解和同理的蘇西,只能靠自己平時的努力工作,來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從復健科自費功能整合門診、共頻治療(Frequency-specific Microcurrent,FSM),到紅繩懸吊,零零總總加起來一個月兩萬跑不掉,才剛賺到的薪水一轉手就又交給了醫療體系。「現在都是拿薪水來看診啦!」蘇西苦笑著說,需要不斷為自己的疾病超前部署,如果政府願意將纖維肌痛症列入重大傷病,就比較有勇氣向別人訴說自己的狀況。
蘇西也認為,即使自己是樂觀的人,面臨一整年疼痛爆表的日常,其實也早恨不得結束生命。因為實在太痛苦,早想一了百了的她,還曾因為把自殺計畫說的太具體,把「張老師」輔導員嚇哭。
「被大家承認」是許多像蘇西一樣的纖維肌痛症患者,心裡最深切的渴望。
若患者的疾病能透過列入重大傷病為社會大眾所理解,政府也能同協助重大傷病病患一樣的方式,協助纖維肌痛症患者媒合工作,讓有工作能力的患者獲得成就感。每日一睜眼,就須與疾病奮戰,「如果再被剝奪成就感的話,就只剩絕望了······」她輕鬆的語氣卻像根銳利的針,一語刺進身患不被認可疾病的患者,心中最痛苦、最痛苦的點。
不過醫師孫維仁也點出了纖維肌痛患者,在要申請列入重大傷病的困難之處,是在於「疾病的不可見性」恐會產生非病患惡意詐病領取補助。他強調,衛福部對此並非不同情,只是纖維肌痛症用現有的標準檢視,仍不符合重大傷病的定義。孫維人指出,其中一大原因是因纖維肌痛症的症狀,舉凡痛、累、煩等皆十分主觀,有心人士很容易偽裝。
對此,蘇西坦言,要認定患者真的有不舒服確實有一定難度。「日常生活真的很辛苦······如果病人真的很常回診,可以從健保使用頻率或看診紀錄來確認啊。」蘇西講話的聲音變得愈來愈顫抖,過了幾秒,話筒裡傳出的僅有她斷斷續續地嗚咽。
雖然路途艱辛,但只要有重大傷病等相關證明,就能少掉了自己為了疾病所必須做出的遮掩和偽裝。在求職之路上,或許也不會再像過往那樣坎坷。「雖然可能還是不會受聘用啦,但比較有依據!」林瑋看著手裡裝著花茶的紙杯,輕輕笑了一下。
學習與「痛」共存,雖然能夠和平共處不代表治癒,但至少飽受身心折磨的纖維肌痛症患者們得以看到隧道彼端那麼一點的光,而這對他們來說,或許才是最重要的。
延伸閱讀
後疫情旅遊趨勢觀察:「慢遊」、「workation」、「旅遊房產」成熱門關鍵字
【音樂】緬懷Meat Loaf:美式搖滾歌劇的最佳代表,成功將自己塑造成「美女與野獸」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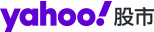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