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詩萍》這家人,集體書寫了「劉樹田先生」的故事,必將是台灣歷史的一個註腳

【愛傳媒蔡詩萍專欄】說來人生也真是有很多的的巧合。
但巧合之間,又彷彿牽連著一些必然的因素。
我去郭重興社長為他母親開的書店,聽長笛演奏。
結束後,跟一些來賓閒聊,其中一組人,都與「樹梅基金會」有關,而這個基金會曾經關切過獨立書店的議題,我很感興趣於是多聊了一會。
我後來寄了本書《我父親》給基金會的董事長劉鎧,想說基金會既然是從他父親母親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組成「樹梅」,那《我父親》一書當見面禮,也算恰當。
孰料,不久之後,我便收到一本非常好看的書《忘記書》,作者是一個家族的後代,集體的創作,主題是懷念他們的父親/爺爺/外公/公公,而主角都是那個人:劉樹田先生。
「樹梅基金會」董事長劉鎧,在書裡夾了一張字跡漂亮的紙條,上面寫著:…回贈《忘記書》,這是我們兄妹試著拼湊父親的一生所寫出的……
是啊,這本書列名的作者,多達十一人,「小自小學生,大至企業家」,絕大多數,是《忘記書》的主角,來自東北的劉樹田先生的家人,少數則是他朋友的後代或劉家晚輩的朋友。
這種集體創作以紀念逝者的合集,本來也算常見,但,這本《忘記書》,最特別,可能也是最好看的部分,是劉樹田先生的家人,在他失智之後,多方去蒐羅他的往昔經歷,而後,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手法,讓「劉樹田」這個人,以「我」為敘述的主角,回顧了東北童年的往昔,在北平目睹共產黨進城,而家人被迫出亡的命運,也回顧了抗戰期間,「我」在後方的青春歲月,初戀故事,以及,國共戰爭後,選擇渡海來台,在台灣重新開始一個家族的飄零與扎根。
劉樹田先生與我父親很像的,當然是,離鄉背井,逃難渡海,來到台灣,而且,娶了台灣姑娘(他娶了原住民,我父親娶了客家女。);但,不一樣的,是劉樹田先生幸運的,能與家人一塊來到台灣,而非像我父親,或很多隻身來台的外省籍年輕人,是孤零零的。
我的父親高齡九十六了,健康當然不好,卻仍健在,只是記憶不那麼準確了;然而我在寫《我父親》時,就已經感覺到,很多事,不容易問出脈絡。
而劉樹田先生則是失智,使得他的家人,在警覺到這將是一條不歸路的同時,想追索一些「關於父親」的來時路時,已然非常艱辛了。
這本集體創作,既代表了家人的不捨,不甘,也試圖在多方的視角下,去拼湊「劉樹田這個人」的生命軌跡。
從大歷史的角度,每個人都很容易被「放進一種歸類」裡,所謂1949年後「來台灣的外省人」即是。
可是大歷史,不足以具體而明確的,描述「那群外省人」的集體名詞下,每張「個別臉龐」裡的哀傷與憂愁。
於是,「書寫個人」無疑是彌補大歷史之過度概括的最好策略。
我寫《我父親》是這樣的理念出發,劉樹田先生的親人,要集體紀錄他,同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
也許,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最終也不過是作為大歷史概括的一個註解而已,可是,對我們這些後輩而言,「每個父親平凡的一生」已經是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最堅定的決定因素了,「沒有父親」就「沒有我們」!
劉鎧董事長太客氣,說《我父親》令他淚流,而我呢,同樣在《忘記書》裡,眼框不爭氣。
也許未必是我們寫得好,而是,我們早在那樣的,父親從年輕到衰老的過程中,直到他們老去,我們才在自己身上的,發現了一種遺傳自他的習性,他的音容,他的個性!那是我們終其一生,不能忘懷的「屬於我們父親的基因」。
我們都該趁早,為自己的父母,留下我們重新認識他們的紀錄。
我們那麼愛他們,卻常常在他們逐漸老去,或驟然逝去之後,才驚覺到:我們知道的並不多,我們示愛的卻那麼吝嗇!
劉鎧董事長一家,為我們示範了一種可能:無論如何,要我們的家族,紀錄下屬於我們從何而來,何以至今,未來如何的線索,那將是這座島嶼之歷史的一個小註腳,可是很多的註腳往往就是大歷史的一段橫切面了。
謝謝劉鎧董事長的贈書,我讀完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經授權刊載,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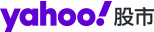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