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布機/兩木金
兩木金
近來,母親住在鄉下的大姐家。
前不久,我去大姐家看望母親,正巧碰見大姐在家裏織布。大姐坐在織布機上,雙腳輪流踏下踏板,兩個繒便分出高下,均勻穿過繒眼的經線便被分成兩層。大姐左手將線梭子從兩層經線中扔過,雪白的緯線便從左至右交錯穿過五顏六色的經線。隨後,大姐右手哐當一聲,用力拉動機杼,將經線和緯線壓緊。這樣的動作來回反復,一匹五彩的帶著各種圖案的粗布就逐漸呈現在眼前。但見大姐雙腳上下踩踏踏板,雙手輪換操作梭子和機杼,動作輕盈美妙,如同彈琴。
母親年紀大了,再也無力操作這臺織布機了。她坐在一旁,癡迷地看著大姐織布。
“這是咱家的那臺織布機嗎?”我問母親。
母親點點頭,笑著說:“就是的,它比你年齡還要大,用了六十多年了!”
我很驚訝地問大姐:“用了這麼多年,這臺織布機還能用嗎?”
大姐滿意地說:“可以的,很好用。”
當年,我爺爺奶奶、大伯家和我家還在一起生活。一大家子十幾口人,穿衣服費布料。因為伯父母兩人都是教師,伯母無暇做手工,所以一家人穿衣全靠我奶奶和我母親婆媳倆紡線織布,手工縫製。每次織布,母親都得向村裏鄉親借織布機。那時候,莊戶人家少有織布機,想順利及時地借到織布機也不容易,往往需要提前一兩個月預約。為了解決織布機的難題,我爺爺想到讓當木工的小姑父給家裏做一臺織布機。於是,我爺爺砍倒了門前那棵一人都摟不過來的洋槐樹。那棵大槐樹長了多少年,我爺爺也說不清楚。他只記得小時候常爬上那棵大槐樹摘槐花,做槐花麥飯吃。
就這樣,小姑父用那棵大槐樹做成了這臺織布機。這是一臺全手動、純木料製作的織布機器。織布機形似木床,高約一米七,總長一米八,寬度有九十釐米,主要由主體、梭子、擋板、踏板、繩索、滾筒等組成,木料厚實耐用,笨拙中顯現古樸。人坐在織布機一頭兒,腳踩踏板,手穿梭子,手腳配合巧妙,將經緯線緊密擠壓在一起,一絲一縷地織出各色布匹。
後來分家時,在母親的要求下,我爺爺將這臺織布機分給了我家。
小時候,我很喜歡看母親紡線織布,感覺那很神奇,總想看個明白,經過壓花、彈花、紡線、染線、經線、刷線、做繒穿線、吊機、再經過拴布、織布等十幾道工序後,那一大包袱潔白如雪團的棉花,就變成了一匹匹或白或灰或黑的各色布料。
在那個年代,冬天農閒時,母親便會紡線織布。晚飯後,母親點起煤油燈,把紡線車放在炕頭上,將彈好的棉花用手搓成如麻花一般粗細的長條,整齊地擺放在一個小小的籮筐裏。母親右手搖動紡線車把手,紡線車便會飛快地旋轉起來,左手拿起棉花條,輕輕地撚出一絲線頭,在轉動的軸頭伸出的杆上一繞,然後慢慢往後拉線頭,一條細細的棉線便纏繞在滾筒上。在昏暗的煤油燈光下,紡線車發出嚶嚶嗡嗡的聲響,如同催眠曲一般。聽著這聲音,我和姐姐們躺在熱乎乎的火炕上,一會兒便昏昏欲睡了。有時候,我半夜爬起來,看到母親仍在不知疲倦地紡線。
經過好幾個月的辛苦勞作,母親終於織出了花花綠綠的布匹。那時候,家裏沒有縫紉機。母親手很巧,將織好的粗布手工縫製成全家人的衣物。母親織的布匹,家人穿衣是用不完的。父親便把這些布匹拿到集市上出售,買回來油鹽醬醋等生活用品。
有一年夏天,全家人在地裏收割麥子。母親的上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已經有幾處裂開了口子,褲子的屁股和膝蓋處也有補丁,顏色不一。我看著非常彆扭,便問道:“媽呀!這些衣褲有那麼多的補丁,真難看。咱家有那麼多你織好的白布、黑布、藍布,你咋不做身新衣服穿呢?”
母親笑著說:“夏天熱,舊衣服穿著涼快。”
我不悅地說:“衣服補丁太多,羞死人了。紡線織布不穿新衣服,留著新布幹啥,能生崽子嗎?”
母親又笑了,說:“布不能生崽子,卻能生錢。你和四個姐姐下學期的學費、家裏的花銷都指望它呢。”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那時候,農民的負擔還是很沉重的,不但要把夏秋兩季莊稼打的好糧食上繳給國家,還要交鄉、村兩級提留,以及教育附加費,所剩下的糧食也就勉強夠全家人的口糧,平日裏的花銷自然是捉襟見肘。
我憤憤不平地說:“你啥時候能穿上好點的衣服呢?”母親寒酸的穿著讓我感到很難堪。
母親滿懷希望地說:“你要好好讀書,以後學成了,當個公家人,把頭鑽進洋面袋子,能掙錢了,媽就再不穿這破爛衣服了。”
努力讀書才能過上體面的生活。從此,這個觀念在我幼小的心靈裏便紮下了根。這或許是我日後將讀書作為一生追求的最原始動力。
織布就必須得紡線,紡線就得有棉花。在很長一段時期裏,父親每年都要種幾畝棉花。種棉花是很費氣力的農活兒。棉花害蟲很多,且生命力都極其頑強。棉花從小苗到開花,一直都有地老虎、金龜子、棉鈴蟲等在禍害,需要隔幾天就要噴灑一次農藥。那些年雨季多,棉株耐旱不耐澇,都長得又粗又高,但開花很少,棉花產量很低。
父親聽說棉稈皮能賣錢,就等棉稈老後拔下來,用架子車一車一車拉回家。在棉稈未幹之前,全家人要將棉稈皮剝下來。剝棉稈皮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要先從根部折斷,再小心翼翼地一點點將皮扯下來。三四畝棉稈,全家人齊上陣,廢寢忘食地剝四五天,才能剝完皮。
棉稈皮裝了滿滿一架子車,如小山包一般。賣棉稈皮當天,為了能夠在一天裏趕回家,父母親和姐姐們一大清早就拉車出門了。父親拉車,大姐在架子車前綁一條長繩,用肩頭拉著繩子的另一頭兒。母親和二姐、三姐在後面推著車。他們五個人一起去縣城的造紙廠賣棉稈皮,一路上捨不得花錢買飯吃,就帶著幹硬如石塊的冷窩頭,走將近十公里路程,才能到達縣城。
等賣了棉稈皮回到家裏,天也就快黑了。一車棉稈皮能賣兩三百塊錢。這對於當時我那個整日為錢發愁的家庭來說,可以說是一筆鉅款,在很大程度上,能暫時緩解一下家裏的饑荒。
後來,家裏的經濟狀況一天天好轉。我們不再穿母親手工縫製的粗布衣服,都買漂亮的的確良、滌卡成衣穿了,但母親還是要堅持紡線織布,儘管這時候,家裏已經不再需要靠賣布補貼家用了。
等到我在城裏工作後,依然喜歡在床上鋪母親織的粗布床單,它透氣吸汗,睡在上面很舒服。
見我喜歡,母親有時候也會紡線織布做床單,讓我帶到城裏,說:“你用不完,可以送給同事或者朋友,別看城裏人啥都不缺,但稀罕咱農村這東西。”
紡線織布工序繁瑣,全靠手工,特別累人。母親年事已高、身體虛弱,不適合再從事這項繁重的體力勞動,況且在城裏集市上很容易能買到粗布床單,也不貴。我不忍心母親受那份勞累、遭那份罪,就勸她別再紡線織布了。
母親一直在堅持紡線織布,說:“現在棉花貴了,賣的粗布床單很少有純棉的,還是自己紡線織布做成的好。”
後來,母親老得再無力紡線織布了,就讓大姐把織布機搬到十裏外她的家裏去。這樣,大姐就繼承了母親的手藝,在空閒時紡線織布。
這次,我看到大姐織布技術嫺熟,再看看白髮稀疏、滿臉皺紋如溝壑般,連走路都顫顫巍巍的母親,百感交集。我撫摸著這臺經歷了一個甲子滄桑、邊邊角角都被磨得又光又亮、為家中做出很大貢獻的織布機,思緒萬千。母親一生為兒女們辛苦操勞的場景,一幕幕浮現在眼前。母親紡線織布時,紡線車發出的嚶嚶嗡嗡聲和織布機發出的哐裏哐當聲猶響徹耳畔。
看到大姐織布,我想起了外甥女靜靜,問大姐道:“靜靜會紡線織布嗎?等你老了,何不把這臺織布機留給靜靜?”
大姐笑著說:“她不會紡線織布,也懶得學。現在年輕人誰還學這古董玩意兒。我織好的粗布床單,人家都嫌難看,不要。”
我心中不免生出些許苦澀的失落感。是呀!農村現在會紡線織布的婦女越來越少。也許有一天,等大姐老了,不能再紡線織布時,我家的這臺織布機就真的該退休了。這件見證了母親一生辛勞的家什總有一天會被冷落,甚至會被遺忘,但是母親對家庭的無私付出,會永遠牢記在兒女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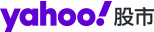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