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主編精選〉台北.我的家
文/圖 蔡莉莉

「妹妹好勇敢喔!」醫生一面打麻醉針,一面讚美我。五歲的我,還來不及驕傲就昏過去。醒來,只記得天花板上那盞好大好圓的燈。
術後必須回台大醫院復健,媽媽把我託付住台北的乾媽,便回台南教書。每天黃昏,隨乾媽的婆婆至頂樓收衣服,我認定遠山背後就是家,到現在還記得那顆看了就想哭的夕陽。
乾媽的婆婆很老了,我喚她奶奶。白天,家裡只剩老人和小童,賣菜車一來,奶奶便從陽台垂下小塑膠籃,籃中置一小石壓住鈔票。菜販依奶奶從四樓傳來的指令,放入蔬果和找錢。我們一老一少便像汲取井水一般,小心翼翼地往上拉。
上了小學,每年寒暑假仍須回醫院校正我那隻不專心的左眼。那一段清晨摸黑搭七小時的火車顛晃到台北的長路,常使我想把家放在拖車上,連人帶床載到台北。直到青春期,我的視神經已協調固定,才結束這段南北往返的日子。
國中畢業到台北讀師專,五年皆須住校,六人一室。室友幾乎都是台北人,很訝異她們從未搭過火車。第一年,我的衣物、壓歲錢,經常一聲不響就離家出走,對十五歲的我而言,那真是一段不容易的時光。初上台北的我,眼中沒有壞人。
週末,室友們皆返家,空蕩的寢室只餘我一人。女生宿舍流傳的鬼故事讓長夜更長了,傳說夜半時分,跳樓的學姐會飄盪在女廁,嚇得我寧可憋尿也沒勇氣到走廊盡頭上廁所。常趁舍監入睡後,偷打開寢室大燈,即使室內亮如白晝,仍徹夜撐著疲倦的雙眼,也不知在戒備什麼。
寒暑假時,我終於可以回台南安心睡覺,在滿桌的意麵肉圓鯽魚鱔魚虱目魚當歸鴨臭豆腐中,得到夠用半年的補給與修復。如此飽食終日直至假期過半,媽媽便要我回台北繼續上畫室,於是,我又借住乾媽家。
那時,乾媽已從靜巷公寓搬到大馬路旁的電梯大樓,我和奶奶同住一室,我睡上鋪,她睡下鋪。每天我從畫室帶回一幅石膏炭筆和一張靜物水彩習作,獨自在家的奶奶,總是用我聽不太懂的江蘇腔國語讚美我的畫。
一回,與奶奶說起在國劇社學唱《拾玉鐲》,她便打開五斗櫃,從紅色絨布小袋中拿出一個玉鐲,告訴我她曾經有一個美麗的么女,在差不多我這麼大年紀的時候,走了。「逃出大陸的時候,我一定要把她的鐲子帶出來。」奶奶話語剛落,眼淚便滴在玉鐲上。十六歲的我,未曾遭逢生離死別,無從想像奶奶的心情,也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語,心底有點詫異一個老母親的哀傷會如井般深長,即使歲月已流過四十年。
踏出校園,迎接我的是台北的遊牧人生。我和姐姐合租一個房間,與房東同住,不能用廚房,餐餐外食。房東太太在自家地下室代客修改衣服,每日為上夜班返家的房東先生煮宵夜。一陣陣食物的香氣竄入房間縫隙,不斷分泌的口水夜夜淹沒我的睡意。
兩個月後,房東皺著眉頭,一臉憂心的通知我們一個月內必須搬家。原來他只是二房東,房價狂飇,屋主急售這棟緊挨著瑠公圳,前院種著九重葛玉蘭花,後院還可晾衣曬被的一樓公寓。
房東決定咬牙購屋,不再分租。我和姐姐每天下班後四處尋屋,像兩隻寄居蟹急於找到下一個遮風擋雨的殼。每當天色轉暗,望著遠方一窗窗溫暖的燈火,所亮之處皆與我無關,站在台北街頭,四顧茫茫,不禁生起無處棲身的喟嘆。
後來,我和姐姐匆匆向一對年輕夫妻分租了一間套房,他們也是二房東,依然多所限制,不能用廚房,不能用洗衣機。彼時,我重回校園,每個星期日帶著在畫室打滾一天的油畫顏料和亞麻仁油氣味,回到租屋處。晚上,終於得空在洗衣板上搓揉那已堆成小山的衣服,心裡總是嘀咕:為什麼不發明免洗衣?
當朋友介紹小碧潭邊有整層公寓出租時,我和姐姐毫不猶豫地立刻搬到那個客廳空蕩得可以跑步,還有廚房可以煮食的大屋子。添了冰箱和洗衣機之後,我第一次在台北看到家的模樣。
某天,路過租屋佈告欄,看見一張「二手傢俱急售」的紅單,遂登門尋寶。小腹微凸操外省口音的主人說:「我們要移民美國,屋子裡看到的,全部隨妳們搬。」最後,我和姐姐以幾乎免費的價錢,搬回一屋子床桌椅燈,連一台十六絃的古箏都跟我們回家了。
二十五歲那年到美國讀書,出國前,將身邊細軟打包寄回台南。一眨眼,落腳台北已十年。
初抵洛杉磯,第一位房東是台灣移民的外省老太太,每天不嫌煩地叮嚀我,洗米水一定要端到屋前澆花。她經常撿拾我切完玉米粒之後丟進垃圾桶的梗子來熬湯,這動作總讓我想起米勒的〈拾穗〉。每當我炒最後一道菜時,她便像背後靈般,緊緊相隨,不斷提醒我:「別關瓦斯!別關瓦斯!換我炒。」根據她的說法,這樣做可以節省打火石的壽命一次。地下室還有一台她藏的超市推車,她說:「反正還會去買,不用還。」一生籠罩在逃難陰影下的房東老太太,即使擁有房產,又已從台灣逃到她認為不會有戰亂的美國,仍不改囤積和克難的習性。
一年之後,租約期滿,我和先生火速搬離,住進一房一廳的出租公寓,終結房東老太太無所不在的雷達干擾和無窮無盡的絮絮叨叨。不再和房東同住,生活上自是自在許多,我們小小的客廳,假日經常聚集了許多單身的台灣同學,有家鄉味的廚房,就是異鄉遊子共同的家。
有一段時間,一位剛從東岸完成學業打算在加州謀職的朋友,暫住我家客廳。我十分好奇她如此渴望留在美國生根的原因。
「難道妳不想回台灣嗎?」我問。
「我們外省人從大陸逃到台灣,不會把台灣當成家。頂多,只是個中繼站吧?」
「可是,妳不是在台灣出生的嗎?」據我所知,她從未去過大陸。
「是啊!但是,我對台灣沒有故鄉的情感。爸媽傾盡所有讓我留學,就是希望我想辦法留在美國,然後把他們接過來。」她語氣堅定的說。
「對我們而言,美國才是最終的、最安全的落腳處。」原來,我們雖然來自同一處,鄉愁卻各自一方。時代是莫之能禦的洪流,生命的劇本裡,每個人或有已設定的角色和不可逆的路徑,是好是壞,各自承受。
五年的洛杉磯歲月,複製了台北一次又一次的遷徙,令我懷疑自己是否吉卜賽人投的胎,內建流浪者的浮萍基因,就像米蘭.昆德拉說的,永遠無法逃脫生命的主題,以為的「新生活」,只是用似曾相識的東西所譜成的一曲變奏。
完成學業,返台定居,碰巧又租回出國前住過的那間公寓。熟悉的三房兩廳,窗外灑入的陽光、清晨五點樓下豆漿店鍋爐的碰撞聲,在台北生活過的證據全都回來了,彷彿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台北之於我,變成家鄉般的存在,想起米蘭.昆德拉所寫:「一個人年輕的時候,看不出時間像個圓圈,反而覺得時間像一條直直的路,永遠帶著他走向不同的遠景;他沒有想到,他的生命只有一個主題;關於這一點,他要到後來才會明白。—直到,生命譜出最初的變奏。」
三十五歲那年,在台北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那一間一間曾經租過的房子,宛如我的生命史,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刻記不同的切面,一次又一次地打磨我對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的渴望。
交屋的那一刻,彷彿找到和台北嫁接的方式,我與台北,終於打了一份家的契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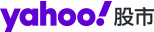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