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線上的法與情系列之一】有了病主法,生死就能自己做主嗎?

當你躺在床上,生命即將告終,你希望用什麼方式向世界告別?插滿管子、積極搶救?還是遵循生命法則自然終結?在你喪失自主意識之際,誰能擔任你的醫療代理人?
對於生命的大限,有人積極面對,預做妥善安排,從容地劃下生命句點;有人避諱隱瞞,讓焦心悲傷的至親伴侶手足無措,無法圓滿安心。去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帶你認真面對臨終的生命主控權。
8月下旬,位於中和的南山放生寺大殿擠滿人,他們不是為了參加法會,而是來認識死亡。當有天生命來到盡頭,會做出什麼選擇?
「這若是阮老爸,伊會好命。」對著寺內滿滿的聽眾,醫師陳秀丹演講一開頭,就提到剛過世的前總統李登輝。「今年2月8日,老先生吃東西不小心嗆到,吸入性肺炎送院,他心臟不好,合併急性腎衰竭,17號那天,他在病房坐輪椅曬太陽,突然間心因性休克,不動了。其實這樣走也不錯,很可惜老先生沒有交代不要插管急救,他就被急救了。年紀這麼大被急救很辛苦,人(意識)不清楚還洗腎。」
陳秀丹是宜蘭陽大附設醫院胸腔內科醫師,出身重症病房的她,以推動善終與安寧療護著稱。豐富的臨床經驗讓她不難揣測李登輝先生臨終的情況。「如果他被急救後不要洗腎,他早死了;血壓掉,不用升壓劑,他也死了;不要用這麼多抗生素,他也死了;停掉呼吸器,他也早就死了。」陳秀丹認為,可能是因為面對這樣位高權重的人,醫療團隊不敢讓他就這樣走了。
無獨有偶,另一場在8月舉行、主題為「生死抉擇」的牙醫師繼續教育課程,也以李前總統的臨終為例,「李登輝接受維生醫療5個多月,這中間很多時侯都可以中斷治療,但是沒有,這就是抉擇。」曾在馬偕醫院教醫學倫理的醫師江盛說,李登輝曾經大氣說道:「我是李登輝呢!哪會驚死?」現實結果卻非如他所願。可見,「當你失去能力時,是仰賴別人代理主權,那可能已經不是你的意願了,而是代理人跟醫師互動的結果。」

李前總統的死亡,引人深思生命尊嚴與自主的意義。去年1月6日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簡稱《病主法》),試圖要面對處理的,就是病人在最後生死一線之間,有沒有權利、可不可能自己決定不再接受醫療,轉而走向生命自然終結這條路......如果他不能決定了,誰可以替他決定?
在台灣,絕症或重症末期病患能不能自主決定死亡,是一個由觀念到做法逐步開放的過程。2000年通過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以下簡稱《安寧緩和條例》)是一次重要突破。接著2016年立法完成,2019年正式施行的《病主法》,更把施行條件大幅明確化(見圖表),堪稱台灣社會討論「生與死」議題的重要里程碑。

看父親中風20年,婆婆臥床12年,阿慧(化名,56歲)真的怕了,近幾年,她很積極地跟先生討論「當生命接近臨終,要選擇怎樣的醫療?」這是《病主法》的核心議題。醫學、情感和人倫,組成各種難題。
避免家人到時放不了手,自己要預先做主
阿慧的爸爸51歲中風,此後20年內,反覆中風,病情一次次加重。最後幾年他臥床、插鼻胃管、無法講話。阿慧的媽媽跟弟弟在家輪流照顧他,每次父親病危就送急診,病況穩定再回家,全家陪著父親穿梭在加護病房跟普通病房之間,很辛苦,父親也受盡苦痛。
幾年後,這種痛苦又折磨著婆婆。
阿慧的婆婆腦血管破裂那天正在旅行,他在車上開心哼歌,突然頭痛欲裂嘔吐,送醫院開刀後,再也沒有清醒過。先生跟小叔要上班,將母親送到養護中心。家人無法一直待在那裡看著,阿慧的婆婆就任人處理。他也是不斷進出加護病房,最後氣切;肢體因長年臥床攣縮僵硬,腳最後竟因一次翻身被折斷,最後,整個人因水分無法排除而腫大,幾乎不成人形。阿慧說:「很沒有尊嚴。每次去看她,我都不知道怎麼幫她,非常難過無助。易地而想,如果是我,我要這樣過日子嗎?我當然不要。」
阿慧只要想起婆婆生前愛漂亮,打扮得端莊優雅的模樣,就很感傷,「我們後來回想,為什麼不讓婆婆自己決定要不要開刀?而是子女做決定?如果當初讓婆婆自己決定,或許他不願承受這些後果。」阿慧說,婆婆開刀前意識清楚,醫師當時跟家屬說,如果他不開刀,1個月走;如果開刀,可能開刀中會走,較好的狀況是坐輪椅或是變植物人。兒女決定讓母親開刀,擔心母親情緒激動影響開刀,並沒有告知她病情。「當時婆婆彷彿有預感,早把首飾分給我們,但是兒女隱瞞他的病情,反而讓他喪失自主權。」
阿慧夫家和娘家人面對同樣的艱難處境,因為父母沒有事先表達意願,兒女不敢不救,也捨不得放手。就像阿慧家人後來有共識,不要再急救了,可是當父親一有狀況,還是立刻送醫院搶救。
病人生前的意願,對家屬往後決定是否不進行維生醫療非常關鍵。因為許多家屬為病患決定後,往往抱持罪惡感。70歲的明月只要談到10年前,決定不為糖尿病末期的媽媽洗腎時,仍淚流滿面,「我媽因糖尿病皮膚脆弱,一翻身皮就破,全身到處潰爛。醫師說,母親的器官都壞掉了,眼睛不會睜開了,洗腎只是維持一息尚存。我不放手不行。」一想到放手就沒有媽媽了,但是如果讓媽媽洗腎,她就可以再撐一陣子,明月為此很掙扎。她問醫師:「如果這是你母親,你會怎麼決定?」醫師搖頭說:「我不會救,我會放棄。」
明月哭著說,「我是大姐,弟弟妹妹都聽我的,那時壓力真的很大,我跟我媽說,『我不是不救你,而是看你太痛苦了。』」母親走後,明月好長一段時間都懷疑是不是對母親見死不救,直到學習佛法重新認識死亡才釋懷。明月一生未婚,擔心自己未來讓弟弟和妹妹難為,她早已寫明自己的臨終意願,拷貝蓋章給弟弟妹妹一人一份:日後,不要做無謂的急救跟治療。

醫師黃軒在《還有心跳,怎會死》一書提到,現代人大部分死於慢性病,其中10個有8個是心臟病、中風、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肝硬化跟阿玆海默症。這些慢性病侵蝕人的器官,逐漸損耗人的生命力,當病人有天倒下,又因為醫學防守太成功,於是死亡像文火,成為漫長的煎熬。像心肺復甦術(簡稱CPR),讓急診如虎添翼,對發生意外的年輕人或器官相對健康者,是加分醫療,但是如果對象是病重老人、重症患者,如癌末,醫療束手無策時,CPR反而增加病人臨終的痛苦,最後病人死狀淒慘,家屬內心嚴重受創。
但現在,如果一個人健康或意識清楚時事先簽下了預立醫療文件,上述狀況都可以避免。
預立醫療決定前,要先參與諮商
初春3月這天午後,阿慧跟小徐夫妻兩家9口人,浩浩蕩蕩來到宜蘭陽明醫院。阿慧決定今天要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阿慧說:「當初,我們無法放下對父親的情感,但是最痛苦的是病人,所以要事先為自己未來的臨終醫療做決定。」阿慧的奶奶跟大伯走之前也是中風,不想像他們這樣,阿慧要預先決定自己想要的人生終點。
這一趟是與醫師陳秀丹的「醫療諮商」,是病主法規定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前的必要程序。但會有這麼多人來,阿慧始料未及。原本他只約先生跟朋友小徐夫妻,但到醫院前的餐敘上,阿慧獨居的表哥羅瑞林、羅瑞林跟阿慧的媽媽,一聽到都說要順便簽一簽;小徐的父母和念大學的兒子也都來了。
小徐的媽媽坤漳嫂說,「我女兒不敢跟我說要簽這個,做兒女的怎麼好跟父母說,自願不要救?但是,我想簽這個好久了,真的是看太多人拖著很艱苦,會驚。」他提到某個親戚因肺纖維化無法離開氧氣,每天灌食,在呼吸照護病房住了8年才走, 「樓仔厝花掉一棟。他的兒女也知道,若是拿掉呼吸器,他早死了。」快80歲的坤漳伯在一旁用台語搭腔:「有健保後,鄰居親友好多這種情形,死袂去(想死死不了)。像有鄰居車禍,救回來,但是都不會動,撐了好多年,他老婆跟兒子都說:『當初不要救就好了,多痛苦而已。』」 坤漳伯在宜蘭每天到田裡勞動,一時興起,還會放下農事,跟老婆跑出去玩。他的生命哲學是:「要能做,好好活。」

為方便跟阿慧兩家人討論,陳秀丹、社工師和護理師決定將諮商移到社福會議室外面的大桌。大家坐定後, 陳秀丹操著一口流利的台語劈頭就說,「台灣醫師是做越多,賺越多,所以你要自己決定你的未來。」夾雜著國台語,阿丹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病主法》,「今天來討論,若有一天生命來到尾聲,像1年內會翹去(台語指死去)的末期病人;第二,不可逆轉的昏迷,就是嘸清楚的病人;第三,植物人,像當年的王曉民;第四,重度失智,就是躺在床上要人弄屎弄尿的人,若是會走會吃,就不是;還有一種就是嘸什麼藥可醫,很痛苦這種,這叫特殊公告的重症,已經不會吃了,要讓人插鼻胃管嗎?要讓人吊點滴嗎?要用抗生素嗎?其實嘸一個人生下來是戴著呼吸器、鼻胃管來到世間,當老到不能吃,病到不能吃,這人生已經嘸意思了。」
簽署前,仔細檢視自己對生命的看法
兩家人七嘴八舌的附和跟討論,慧美的先生問陳秀丹:「這些病人恢復正常的百分比是多少?」她回說:「零。但是有一些醫師會盡力拚。有一些家屬則會跟醫師說,你不救,我要告你!我還有病人領18%跟保險金,家人不讓他們死。這是很悲哀的代誌。」
一聽慧美的媽媽笑笑說著自己洗腎多年,樂觀看待死亡,阿丹說:「會走會跑洗腎OK。不過洗腎的人血管嘸好,很容易臨時出血或心跳停止,救回來的嘸幾個。像我爸以前每次洗腎,我們也是決定若是他洗到一半袂喘氣(指喘不過氣),就讓他走。我常看到病人被綁在床上洗腎,因為他會拉管子,這就嘸意思啊。阮母教我,會吃會走才是好命,要人弄屎弄尿(指需要人把屎把尿),是歹命。」 當年陳秀丹的母親突然倒在浴室,當她在醫院看到母親大腦的X光片,就知道母親即使開刀也不會醒了,於是說服兄姊尊重母親的意願,帶母親回家,送她好好離開。她轉頭跟快80歲的坤漳伯說,「像阿伯閣會下田種菜,開車去賣菜跟迌,才是好命。」
根據《病主法》規定,預立醫療的意願人,需要二等親內如配偶、子女、父母、手足及公婆至少一人參與才能簽。面對這種規定,離婚、如今單身,已經70歲的羅瑞林問:「我老爸過世,老母早改嫁了,而且我絕種了(指沒有子嗣),很多人像我這樣,怎麼辦?生,我嘸法度決定,死,我要自己決定。不是叫病人『自主』權利法,自己就可以簽啦,為什麼還要二等親陪同?」

羅瑞林的問題,答案仍然在病主法裡。他的狀況可以簽「無家屬聲明書」。包括單身、獨居跟家人已沒有聯絡,或家人沒空擋、喪親等原因,沒有親屬可以陪同參加預立醫療諮商的人,只要提出二等親屬無法出席或是無法期待參與之說明就可以參與醫療諮商。但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仍在官網上提醒,預立醫療諮商的意義有部分就是希望協助家屬知悉並尊重意願人的意願跟決定,所以還是希望家屬參加。
如果他們不是夫妻
一位乳癌末期的女病人朱青(化名)由一名男士陪著來找重症醫師黃軒。黃軒看他們「夫妻情深」,坦誠對男士說,太太已末期,避免延長死亡過程受苦,病危時不要插管。兩人點頭說好,最後卻沒簽《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簡稱DNR)。當晚,朱青病況急轉直下,經其他值班醫師急救插管,住進加護病房。黃軒去看朱青時,只見無法講話的朱青流著淚,黃軒很不忍,跟他道歉:「對不起,你不應該插管……」將近兩週,黃軒只看先生來看朱青,卻不見其他家人,非常困惑。
根據《安寧緩和條例》,當時朱青意識不清,可以由家人幫她簽DNR,但是為什麼她「先生」不能簽?黃軒請社工跟心理師去了解倆人的關係跟家庭背景,才知道原來倆人並非夫妻,而是不倫戀的小叔跟嫂嫂,兩人放棄各自的家庭在一起,全家很不諒解。直系家人和真正的真正的先生沒有人願意出面幫她簽DNR,「假」先生又沒辦法簽,一直拖到朱青嚴重感染、心跳停止,黃軒才拔掉朱青的管子。
「好掙扎,好痛苦,好複雜。」黃軒說,他不知道目睹多少類似案例,病人健康或清醒時,沒有為自己未來的醫療預做決定,當病人有天昏迷,醫護人員不知道其意願,只能任由家人決策。如果配偶或直系親屬沒有幫他簽署DNR,或是彼此沒有共識,醫師就只能搶救到底。

黃軒形容,這種「被迫活著」的末期患者非常可憐。如果病人仍有意識,氣切後會無法發出聲音,長時間的痛苦讓他們僅能瞪大眼睛,用眨眼來求救。病人由於施打過多點滴,全身水腫,氣管內的分泌物也增加,抽痰的負擔也跟著增加,很容易反覆爆發吸入性肺炎,伴隨高燒和呼吸困難的症狀,最後痛苦的離開。
朱靑這個極端案例更加呈現病人自主的重要。黃軒說:「如果當時有《病主法》,病人也有事先簽,他不需要插管,連鼻胃管也不需要,就能好好走。」朱青與家人關係破裂,如果事先指定「醫療代理人」,在最後緊急關頭執行他的意願,也可以解決這問題。
最了解病人的,是照護的移工
「他可以指定情夫當『醫療代理人』,《病主法》跟《安寧緩和條例》都可以指定。」聽到朱青的案例時,國健署長王英偉這樣說。所謂醫療代理人,不是「代替」病人做決定的人,而是在充分理解病人對生命的感受、喜好與價值觀後,能從病人的最佳利益做出決定。「同樣的,也可以指定『小三』當醫療代理人。像有人跟『小三』的感情比跟原配好,原配可能還希望他死得越痛苦越好,所以不會以病人最好的方式做決定。」
擔任國健署長前,王英偉在花蓮成立了慈濟「心蓮病房」,一直在部落跟社區推廣安寧照護的觀念。面對台灣25萬名外籍看護,王英偉也問了一個極為實際的問題,「那阿蒂或瑪莉亞(指印尼或菲律賓籍看護)可不可以做醫療代理人?當然可以。他們照顧老人多年,我常看到老人過世,他們哭得比家屬還傷心。」
根據《病主法》規定,因為病人死亡而得利益的,不能當醫療委任代理人,所以不能是器官指定之受贈人,也不能是死後能得到遺產的非法定繼承人。陳秀丹說,「醫療委任代理人就是潛在活得比你久,瞭解你,可以捍衛你權利的人。如果小三跟外勞沒有因病人死亡繼承財產,他們當然可以當醫療委任代理人。」
許多因長期照護衍生的悲劇,透過預先簽署《病主法》,未來也可以減少。

清晨6點,黃軒到呼吸照護病房查房,多了一個病人,阿嬤昨夜從別院轉來。她接著呼吸器,無法說話,但是眼神銳利的跟著黃軒游移,黃軒發現,阿嬤只有眼球會動。
阿嬤是漸凍人,在病房住了3個多月,黃軒從不曾看家人來看他。漸凍人、小腦萎縮跟硬化症等罕見疾病目前都無藥物可以治療,到末期很辛苦。黃軒大概可以猜到,家屬照顧阿嬤到後來已經很疲憊,就不來了。他說:「當你開始生病,假使你家族有40個人,他們會在1週內通通來看你;當你超過20天,可能只剩下20個人會關心你;當你生病超過20個月後,可能只有瑪麗亞會送尿布到呼吸病房來給你。」
阿嬤突然大量血便,黃軒只好打電話給他兒子。一聽黃軒問是否要為她做大腸鏡檢查,他口氣冷淡的說,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為了避免醫療糾紛,黃軒按照醫療常規幫阿嬤做大腸鏡檢查,他說:「如果你不曾看過阿嬤的家人,你敢不做嗎?可能會殺出一個程咬金出來告我。」根據《醫師法》第21條:「醫師對於危急的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違反會有罰鍰甚至刑責。除非是病人家屬事先有共識,不要急救。
但是,台灣因醫病間的不信任,許多家屬不滿意醫療結果,或是因為無法面對家人死亡的悲傷與內疚的情緒,轉而責怪醫師。根據衛福部統計,在2018年,民事及刑事的醫療爭議案件有391件,平均每天有1.07件家屬吿醫師的案子。雖然定罪率低,許多醫師卻都怕了,於是採取防衛性醫療,有些甚至不考慮治療有沒有效益,讓自然死變得更加困難。
黃軒説:「怕哪個家屬有意見,醫師只能先緊急處置再說。如果今天遇到的是有良心的醫師,會告訴家屬,嘗試治療無效,是不是要繼續?但是大部分醫師不會講。」說穿了,醫師也不知道怎麼面對死,更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上。
黃軒幫阿嬤做大腸鏡後,發現她有大腸癌,一顆腫瘤正在大出血。他決定不再幫阿嬤化療跟開刀,因為這些對阿嬤都是無效醫療。阿嬤的心跳跟血壓快沒有了,黃軒通知她兒子,要他派人來接媽媽回家。他說好,沒表示任何意見。黃軒來到阿嬤床邊,看著他的呼吸趨緩,沒力氣撐開眼睛,知道她快死了,他不知怎麼跟阿嬤說,兒子不會來看他,但是也無所謂了。他握起阿嬤的手,輕柔地在他耳邊說,「你的眼皮會重重的,你睡著沒關係,我在這裡陪你。」
「其實插完管後,家人都期待這一天的來臨,可是說不出口啊。」黃軒説,這類罕病病人只要被診斷出疾病時,就趕快簽《病主法》,當最後器官衰竭,連鼻胃管也不用插,慢慢就死亡了。

臨床發現,如果家人平常有分享溝通死亡的事,這樣的病人的確可以接受自然死亡,安詳走完人生。陳秀丹說,其實老天給我們非常舒適的退場機制,當一個人老病到不能吃時,腦內腦內啡生成量會增加,讓一個人比較舒服的離開。「作為一個照顧者,你千萬不要有罣礙。」
「其實一個人的死亡不恐怖,是因為家人的情緒壓力恐怖,才認為病人死亡恐怖。」黃軒認為這種情緒壓力連醫護人員自己碰上都難以招架。他一個醫師學長就為了要不要治療父親跟家人反目成仇,這位學長也是這方面專家,覺得爸爸末期,不需要治療了。沒想到兄弟海外回來,憤怒地質問他,為什麼不等他們回來?是因為財產嗎?
家屬懂得病人的痛苦嗎?
這位醫師在兄弟面前,不是「專業」,而只是個兄弟。正如醫生王安(化名)面對母親,什麼醫療專業都不管用了,他就只是個兒子。
王安的母親臥床多年了。即便知道母親已深度昏迷,兄妹也同意放手,他仍然沒勇氣幫母親拔管。王安說,「我媽生前沒有講過不要插管這些,他那年代沒有這種思想,所以完全是我們子女的主意。但是,我真的無法接受母親拔管,我無法執行……」王安停頓了一會兒,艱難的說著:「我拔不起來,我也知道目前是無效醫療,但我真的拔不起來,抱歉……因為我知道我拔掉5分鐘,她就走掉了。」
每次王安去養護中心,就看到母親包著尿布,只隨便的披著一條毯子,很沒有尊嚴。但是他總是想,母親已經沒有意識了。「母親對我就像棵大樹,雖然他是植物人、機器人,但是至少他還在,我有個依靠。我還能像往常一樣,看診後、疲累時,每周來看看他,跟他說說話。」王安有能力支付母親的養護費,所以任由母親這樣拖著,換成自己,王安卻不希望以後拖累兒子。他説:「我會去簽病主法。」
病人不能走的殘忍原因
看護間常流傳一句話:VIP、有退休金跟保險金的人,都不容易好走。
看護阿純經常看到為了父母的月退俸或商業保險金,不放手的兒女。說到之前照顧的老病人,住礁溪舊街的一位阿伯,阿純仍氣呼呼的。阿伯的小兒子就因為他的18%的軍公教優惠利息,不讓他走。姐妹出來阻止沒用,社工介入也無效。阿伯一次次被插管救回來,瘦到全身皮包骨;每三天拔一次針,拔到皮破,全身在滴水。阿純曾勸他,「老爸在受苦,可以放手了。」沒想到小兒子回他,「能救就救到底,插管可以活,為什麼要讓他死?我多愛我爸爸。」
奇美醫院緩和醫學科主任謝宛婷說,跟這類家屬溝通最困難的是,他們希望病人活下去,是為了他自己,根本不管病患有多痛苦。「所以,當一個人失去自主,要保有尊嚴是非常困難的。」謝宛婷認為如果有簽病主法,再加上碰到有膽識的醫師,不怕家屬刁難,這種情況才可能有解。

許多家屬因為不是自己照顧病人,對病人有多痛苦,似乎完全沒有認知。阿純有時看不下去,會趁家屬來探病時溝通,「他真的很不好了,實在很可憐,不要再給他折磨了。」阿純說:「我們都會去找阿丹醫師幫忙,阿丹才會幫忙這些受苦的老人,讓他們好好的自然死。」
陳秀丹說,有健保後,病人不容易「好死」。以前插鼻胃管是為了病人能好,沒問題。可是現在給一群生命末期的人插鼻胃管,沒有好處。他曾看到有老人一天被重插三次鼻胃管,因為他不舒服拔掉,最後被重插,五花大綁。「他自己拔掉管子就是不要,為什麼要給他重插回去?台灣的老人要這樣被綑綁的晚年嗎?這種扭曲的末期生命照顧,一直是我內心最大的痛。」
真正看見痛苦,才有力量放下。在陳秀丹醫師的建議下,阿慧的先生為母親簽下《安寧緩和條例同意書》,同意撤除維生醫療。最後,陳秀丹為他母親拔掉氣切管,不給藥、不打點滴,也不給水,只給外貼嗎啡止痛,母親終能安祥離世。阿慧安慰的說:「婆婆的身體是柔軟的,他終於回到生病前的樣子。」
(為尊重受訪者隱私,文中阿慧、小徐、朱青、王安為化名)
更多鏡週刊報導
【時代現場】她燒了她的夢 一位醫學生的縱火軌跡
【時代現場】從愛國到愛錢 威權時代黑道維穩紀實
【全文】安樂死的是與非 當活著令人難以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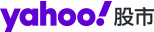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