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世嫉俗

人生停滯不前的感覺,總是在周間特別強烈,當我在咖啡店裡坐下,翻開買來或從圖書館借來的書時,看到社群網站上,我的同學、學長姐學弟妹,都在自己的職位上工作著。
每當想及此,我就會感覺無比地沉重。
提筆開始寫遺族相關的文章、進行訪談的時間,我已經完成在新加坡的課業,也感謝COVID-19,讓我又回到了台灣,進行眼前的寫作計畫、至國外駐村、與創作者交流,其實與我原先設定的人生道路有不小的偏差。本來的預期是畢業、就業,然後把過往的一切都留在過去,人生繼續往前,但我發覺自己前進不了,或感覺自己沒有在前進,我逐漸開始思考,或許是要完成這樣的寫作?
又或者,這是我的悲傷療癒過程。
人類面對悲傷的歷程,從原本的悲傷五階段,到六階段、更多都有可能,精神與心理學家做出這樣的歸結,並不是說悲傷只有這些可能,我想更多的,是希望讓身處悲傷的人,在一團亂的情緒之中,仍有些許辨識自己路途的可能。
接下來是我試圖以震驚、困惑、憤怒與罪惡感、懷抱悲傷、無意義感、緘默等階段來描繪自己的道路,在這個過程裡,怎麼生活、擁有什麼樣的情感。並不一定是按照時序地進行,可能重疊、交替、反覆,但都是真實存在過的感受。
我並不是個習慣表露悲傷的人,尤其在人前,也因此,在母親的喪禮我全程沒有掉下一滴眼淚。
只是我記得,我曾經在新加坡念書時的一次課後時間,大家坐在學校後方的露天酒吧裡喝著啤酒,那天是來自印度新德里的同學G的母親忌日,隨著啤酒的容量逐漸減少(是在新加坡難得可以找到的便宜酒吧,一品脫只要十塊新幣不到,簡直是天堂),我也講起我的故事,儘管在座的大家早已經知道,我當時延了一年才入學,就是因為母親生病、離世。
我說:「想念我的母親。」然後掉下了眼淚,坐在旁邊的好友想要安慰我,但坐在對面的G阻止了她,並向大家擺了擺手,說:「Let her out.」 然後看向我,點點頭,像是在示意我不用停下眼淚,就好好地悲傷。
我是直到很久以後,讀了些許與悲傷療癒相關的書,如《一個人的療癒》,才知曉這是同樣有過失落經驗的人可能才曉得的悲傷療癒方法-不要抑制情緒,不要抑制悲傷,因為它會一直在那裡,如果你不去處理它,它是不會好的。
「隨時間過去」,也是我本來的想法,一年、兩年、三年,但我依舊無法不回到那個當下,我推開浴室的門,發現燒炭自殺的母親。
我還記得那一刻的感受,我心想:不是真的吧?但在心裡頭某一深處,卻又好像早已經知道這一天會到來。
那個畫面就像是電視劇場景,我以為我只是點開了《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陳浩遠想著還想要跟父親說一句話,結果推開門是父親上吊的畫面。雖然當年公視首播,在看見這一集時我深感震撼,多年來我也曾設想過會不會某天看見母親這樣選擇人生的結束方式(然後成了這樣的自我預言),但直到真的面對時,再多的預期性悲傷都不足以抵禦這真實映入眼中的悲傷。
震驚,又或許是會被稱為否認(denying)的階段,我原先以為自己並沒有經歷這個階段的可能,因為許久以前就曾經在母親的日記中看見她早就想尋死,母親還常常說她早就已經買好木炭,我問「放在哪?」但她並不想告訴我。
直到我清理母親餘下的東西時,我都還是沒有發現那包她說她早已買好的木炭,她用的是她當天買好的木炭。
遺族要活得不憤世嫉俗好像有點難,但也許不應該以偏概全,說不定只有我,而且說不定我本來就是個脾氣偏差的人,成為遺族更加容易感覺被冒犯。我的確度過了一段憤世嫉俗的時間(而且說真的也不短),遠比以前更容易被踩中情緒的地雷。
從最一開始,向旁人告知母親的死亡原因時,曾經收過一些讓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的反應。
例如,不是很熟悉的國中同學,在我發文講述母親過世的當天傳來訊息問我說:「妳媽媽是怎麼過世的?」也許、也許她是出自於好意,但在當時的我眼裡,那出自於好奇的窺探讓我覺得十分不受尊重、無禮。又或者是有人問道:「她(指我母親)怎麼可以這樣做?」這讓我不知該怎麼回應,甚至感覺有些戳刺。
只是,依舊也有讓我感覺溫暖的回應,像是在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一名友人用網路與我通話,她在另一頭一句也沒說,就是任憑我一個人講些沒頭沒尾的話,然後抓著電話哭著,但僅有的那一刻讓我知道我並不孤單。以及,在事件後的一個月,與高中同學一見面,她當下什麼都還沒說,就先給了我一個深深的擁抱,然後對我說:「妳一定嚇壞了。」
有的時候,也許想要的不是一再拋擲出來的問題,因為我也真的不知道答案,而且這個世界上,不會有比我更想知道為什麼的人了。
「這是災難性的一件事。」
翻閱與遺族相關的文章、書籍時,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形容,然則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應當有比這還要更符合災難(catastrophic)的事件才是(大型公安意外、傳染病、貧窮問題),但就算我這樣認為,也不代表就能夠淡化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響。
畢竟,它的確是如此災難性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明確感知到,我的人生在母親自殺的事件前後,區分成了上輩子,以及這輩子。上輩子的我,不曾經驗過親人的自殺,就算有,也只是朋友,仍能說服自己那尚遙遠;上輩子的我,有足夠動力,能夠同時做很多事情,例如有正職工作時也能兼任講師、打工、做side project、勤於更新社群媒體,兼課時還自掏腰包準備小禮物給學生,也有力氣去跑馬拉松或各種路跑,完賽後與獎牌自拍,然後把照片用LINE傳給母親(於是我就在母親留下的東西裡,發現了一本相簿,裡頭放著這些我傳給她的照片,她全數洗了出來,收納在相本裡)。母親自殺後的我,這輩子的我,覺得世間索然無味,除了不期盼親密關係,也對人際關係、工作感到倦怠,運動也只是為了讓身體動起來,不知道自己努力是為了什麼──不必孝親,也沒有人世間應負的責任。
我完成學業,卻也沒有進入職場,成為稱職的螺絲釘。
我彷彿不知道為什麼而活著,也找不到繼續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
活著,就只是為了活著。
我繼續每天醒來,然後為自己煮一杯咖啡,出門運動,回來煮午餐,可能看書、可能寫著眼前的字、可能上些看似對求職有助益的課程,然後晚餐,看些劇集後,上床入睡。偶爾有社交活動,但當然限於周末,周間是大家上班的時間。我戲稱這簡直生活滿意度極高,哪門子的理想退休生活。
但我知道不能這樣繼續下去,每一天我醒來,都應當有些理由,而不是就在睡眠中恆久無法醒來。
我必須知道自己留下來的理由,我必須知道這個世界為什麼需要我留下來。
(本文摘自《修復事典》一書,大塊文化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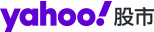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