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台灣的MeToo時刻尚未到來
⊙張茵惠
十多年前,一位女性友人向我吐露遭到完全不熟悉的人強吻的可怕經驗。她因為擔任研究助理而接洽了某位藝文界人士,這個人完全就只是工作上的往來對象,她對他沒有半點了解,更沒有任何私人興趣。然而,顯然對方把女性工作時流露出的好意錯當成了浪漫的訊息,他在四下無人時強吻了我的朋友,並且在她驚駭到全身僵直時,很失望的問:「你怎麼沒有回吻我?」
她沒有通報,也沒有聲張,只是找個藉口落荒而逃。因為她覺得,對方是有名的人,而她只是個助理,沒有人會相信或者在乎她的經歷。但這讓我好奇,對方到底是多有名的人?她猶豫了一下,小心翼翼的說:「你有聽過貝嶺嗎?」
當我發現,貝嶺的受害者不只一位時,我想起我的朋友,想起她跟我說這件事情時的困惑跟受傷,不知道她是否覺得正義已伸張。也許她並不這樣認為,畢竟女性在職場上遇到的不公與傷害,遠遠不只是性騷擾這麼簡單。能夠簡單用一個故事說完的傷害,其實都是相對容易解決的。那些潛藏在紋理之中的加害結構,如果要拆除,彷彿就會連房子一起倒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些有幸不被打破,好好孵育成芻鳥的人,可能會這麼跟你說。
MeToo從來都不是屬於所有人的運動
我們很少能夠親眼目擊歷史時刻發生,並且輕易看出脈絡何在。如果2023年台灣人沒有受到《人選之人》這部戲劇打動,那麼之後當民進黨提名國民黨青年軍出身的李正皓參選立委時,不會引起如此多青年世代民進黨員的反彈。李正皓涉嫌拍攝女友裸照並藉此威脅女友這件事情已經發生很久了,當他2020年披掛親民黨戰袍參選時,藍營似乎沒有人覺得他對待女人的方式是個問題。
而如果民進黨沒有如此遲鈍的提名李正皓,並且天真到以為泛綠女性支持者跟泛藍女性支持者一樣好搞定,民進黨近日不會連環爆出如此多起性騷擾吃案的受害者證言。李正皓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的出線讓當初努力維護「鳥巢不要翻覆」的女性民進黨支持者懷疑,犧牲自己守住這一切到底有何意義?
第一批選擇說出過往的女性,大多都已經早就離開政治工作。與其問,為什麼這些女性現在才說,更應該問的是,她們之前為什麼不說?在職時不能講,或許是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隱忍不發。但去職後也不願追究,難道不也是因為對於守護台灣的價值觀有所忠誠,因此按下不表嗎?當某些人說「台灣獨立跟女性主義原本就互相牴觸」時,我懷疑這些人根本不知道女人長期以來已經為了理念犧牲了多少。
但如果很樂觀的說,台灣終於迎來了自己的MeToo時刻,事實也絕非如此。截至目前為止,男性政治人物、政治工作者在這一波運動中遭到舉報的,絕大多數都只限於民進黨陣營跟貝嶺、王丹之類的外國人。「不抗中」陣營目前只有前任《端傳媒》評論總監跟國民黨幕僚的曾柏文與現任國民黨立法委員傅崐萁受到檢討。
然而,如果你稍微彙整過去幾十年的性侵、性騷擾醜聞,事實上「不抗中」陣營犯下的罪行嚴重程度跟發生頻率都遠比抗中陣營多得多,但「不抗中」陣營的支持者顯然並不太在乎他們支持的政治人物不把女人當人看,就像親民黨支持者不會過問李正皓有沒有拍女友裸照一樣。
正因如此,這波潮流目前看起來並沒有觸發任何深刻的社會體制改革或者男性集體反省的跡象,或許未來會有,但目前沒有。畢竟就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都喜孜孜撿到槍,發一篇臉書貼文得意洋洋的檢討民進黨,彷彿他們自己做得很好,殊不知民眾黨內部遭到性騷擾並且吃案的女性黨工鍾棠芝當天就會發文:「有想過我的感受嗎?為何他黨事件出來隔天就義不容辭相挺?」
此外,發生在美國的MeToo雖然國際能見度相對較高,而被拿來當成女性反對職場性騷擾與剝削的口號,但其本身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有益於改善女性處境的運動依然是個問題。舉例而言,黑人女性並不樂意加入MeToo行列,因為同樣的口號黑人女性主義者塔拉娜‧柏克十幾年前就提出了,而當時社會並不把她們當一回事。另一個問題是,MeToo風口浪尖上的人,都是相對富裕的女性,她們的訴求固然很有力量,而且是事實──所有職業女性都遇過性騷擾,但同樣真實的是,對於更弱勢的女性來說,性騷擾可能遠遠並不是工作時遇到最糟糕的問題。
MeToo運用女性的共同憤怒,將一些有權有勢但為人齷齪的男性暫時拉下檯面,這固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這是否真的成功改變了結構,是否真的拯救了更多女性?又或者,MeToo只是一種對艱困問題的簡易解答,用一種顏色斑斕而且光鮮亮麗的快閃行動劇,去演出「只要是女人勢必同一陣營」的烏托邦幻想,從而逃避了更加複雜跟困難的問題?
性騷擾的癥結在於創造出「敵意環境」
當我們提起影視影響社會的案例時,通常第一時間會想到南韓電影《熔爐》,它激起了民眾超過百萬人連署要求重審電影改編的學校性侵案件,並在隔年催生了南韓的《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相較之下,《人選之人》儘管誘發了近來一連串的事件,但卻不太可能造成法律層面的任何改變。我國早就已經有《性騷擾防治法》,而且2005年就施行了。這套法規並不只要求個人應該約束自己的行為,避免侵害他人權益,更重要的是它也要求政府、學校、公司等等機關單位,應該負起責任,積極避免自己成為「敵意環境」。
必須一再強調「敵意環境」這個概念,是因為社會長期以來對於性騷擾的想像都過於狹隘,有時候根本是錯誤的,譬如認為性騷擾是一種「一對一」的「貞節玷污」,而無法想像有可能是「多對多」的「有毒壓力環境」。某種意義上,性騷擾跟霸凌的運作機制非常類似,都無法只靠受害者跟加害者完成──還需要那些冷眼旁觀甚至合理化加害者行為的第三人,才能拼上全部的加害拼圖。
性騷擾加害者通常都不是「一時控制不住自己」的鹹豬手慣犯,而是知道無論自己做了什麼,都會有人幫他找藉口,認為他「功大於過」的人際關係精算專家。他們很可能確實有幾分能力,並且因此覺得用自己的能力跟地位換取剝削他人不受追究的特權合情合理,換句話說他們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值得這一切,包括享用弱者身體的權利。
更重要的是,性和性別有關的騷擾並不僅僅只是明顯可見且幾乎人人都覺得不可取的偷摸、偷吻、偷抱,而更是透過隱隱的威脅、利誘、排擠、羞辱、言語輕薄、明褒暗貶,來讓女性「明白自己的位置」、「知所進退」,從而顯示她們是「劣於」一般人的一群,不值得獲得全部的尊重。而如果最後,她們放棄了自己的工作,你永遠不會知道她們原本可以提供多少貢獻。
這不僅是對女性而言,男性也可能基於受到上司或者同儕的性騷擾。儘管法規並未缺席,但現實生活中,真正願意使用《性騷擾防治法》的受害者很少,因為付出的代價太過龐大。
說出來之後的復原之路
「說出你的真相」,這句話聽起來非常的強大,幾乎掩蓋了不少當年出書揭發性騷擾與性侵害醜聞的MeToo參與者,日後經常因為必須繼續活在「說出真相後」的世界裡,而接受心理諮商的事實。與旁觀者想像不同是,世界不是一場電影,沒有在真相被說出來的那刻結束。你必須繼續生活下去,帶著你勇氣的榮耀,跟你承擔的後果。
這世界依然在容許男性到處製造讓女人感到「這裡沒有我的位置」的敵意環境,有時候是一個小小的KTV包廂,有時候是一個辦公室,有時候是一整個社會。國民黨人吳敦義因為社會出現分屍案,而指稱是蔡英文總統的性別禍害國家,說她是「衰尾查某」,他從未因此付出代價。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說超過四十歲的女性是殘障車位,並且說女性天生比男人次等,要不是有粒線體 DNA 的話,地位會更低,他也同樣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發言付出過代價。
在上述這些人真心懺悔並且做出彌補之前,台灣的MeToo其實沒有發生。那些受害者鼓起勇氣說出的真相,充其量只是這個月的談資,下個月就遺忘。她們冒著傷害自己政治信念的風險,也想要追求的另一種公平跟正義,對於媒體跟社會來說,就是這麼不值一提。
我不期望全體男性都能打從心底理解,自出生以來就被放置在一個告訴你「你不配跟其他人平起平坐」的敵意環境是什麼滋味。男人經常抱怨當兵的經驗,那我現在可以告訴你,當女人的感覺就像是一輩子都不能退伍,永遠在被長官指教的菜兵。總是有些其實仔細想想能力也不怎麼樣的人在忙著告訴你,你應該把頭低下,乖乖聽令。
當她們挑釁的抬起頭,並且說她們不想再繼續這樣了。這一次你是否能夠選擇站在受暴者的一方,並且理解到──拆除高牆聳立的敵意環境,是我們全部國民的責任?
附錄:〈國民黨與民眾黨之性侵害與性騷擾簡史〉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信仰女性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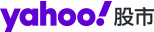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