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包青天披上法官袍! 王泰升揭開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史

王泰升研究員是臺灣法律史權威,研究的日治臺灣司法正義觀轉型,見證了臺灣法制由傳統邁向現代的歷程。(圖片來源/研之有物授權轉載,下同)
從衙門官司到法院相告
走過 120 年光陰,臺灣人的司法正義觀逐漸汰舊換新,過程中經歷了哪些折衝?今日還遺留哪些舊有觀念?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臺灣史研究所暨法律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王泰升,經由日治時期文獻考究,探討司法制度與觀念典範的變革過程中,人們如何理解或想像司法?主政者如何與人民溝通?制度面如何循序改變?當前臺灣的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展開,歷史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連續劇中,衙門差役齊聲大喊「威—武—」,包青天手中驚堂木一拍:「有何冤情,速速道來!」……揉揉眼睛、轉到下個頻道,畫面突然變成法庭上律師和檢察官正激烈辯論:「抗議!誘導詰問!」只見老法官推了一下眼鏡:「異議駁回,律師請繼續。」
從《包青天》轉台到《絕命律師》,恰似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過程。這也是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暨法律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王泰升,在多年臺灣法律史研究中一項重要的成果。
清治時期,臺灣漢人奉行的是傳統中國的上衙門打官司、原住民族遵循祖靈信仰來分辨善惡。二次大戰結束後,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則全面適用西方的現代法律制度。夾在這兩階段中間的「日治時期」,正好是銜接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期,保留臺灣人「司法正義觀」轉型的蛛絲馬跡。
「去法院相告」這樣的說法,在 1895 年日本開始統治臺灣前是不存在的。在傳統中國,這句話應該是「上衙門打官司」。
法院是國家行使司法權的機構,衙門則是官員處理政事的處所;「相告」隱含了兩造平等對抗的意味,「官司」卻是把爭議呈請官員定奪。光從這段話的演變,就可以看出很多基本觀念的變化。
王泰升利用現代法中四個「分立」概念,檢視日治臺灣的司法正義觀如何從傳統過渡到現代觀念,分別是民事紛爭的「判調分立」、民事審判中的「審辯分立」、刑事審判中的「審檢辯分立」,以及國家權力的「司法行政分立」。

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歷程
假扮成調解的審判
現代法中的「判調分立」,是指民眾在面對私法紛爭時,可以循「調解」或「審判」兩種程序處理。前者是由客觀第三人促進兩造「談」和解,法律此時不是重點,以當事人意願優先。後者則由法院依法律做出判決,對兩造都有拘束力,且不一定符合當事人意願。
不過,清治時期的臺灣人沒有當今所稱「民事」、「刑事」概念,不論發生錢財糾紛、家庭衝突或犯罪案件,一律「報官」處理。地方官在處理爭議時,必須以洞悉人情的手腕、因時因地制宜,不必全然依照律例等條文的規定。
現代的依「法」審判,是國家公布施行的「法」;但傳統法觀念中的「法」,卻是「法外施恩」的「法」,正義的最高判準是「人」,而非制度或律例。
因此,臺灣總督府在日治初期,因應新舊觀念的折衝,建立了「民事爭訟調停」制度。形式上是尊重兩造意願的「調解」,實際上調停官扮演了傳統衙門內青天大老爺的聽訟角色,以地方官的權威「指示」當事人該如何和解,透過拍桌厲聲斥責、神前賭咒發誓、或強調因果報應等方式,展現強烈的上對下斷案強制力。

日治時期臺北廳民事調停室的調解景況。調停官糾集相關人士,勸諭站立其前方的民事紛爭當事人相互讓步以達成和解,扮演類似清治時期衙門官吏的角色。 資料來源|《臺法月報》2:10(1906 年 10 月),頁 113「本島の民事爭訟調停成績;附圖臺北廳民事調停室の圖 一記者撮影;附表」,漢珍數位圖書公司提供。
於是,判、調間的分際被刻意模糊。雖然引進新觀念的衝擊降低,但也意味著臺灣人對於「判調分立」的原則,更加難以理解與接納。
訟師?律師?兩者有何差別
在民事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後,依現代法觀念,必須落實「審辯分立」,也就是原告與被告需各自委任專業訴訟代理人(亦即律師,日治時期稱為辯護士),好為自己找出最有利的法律來適用,再由法官依雙方陳述來審理。
但在傳統清治社會,報官的人民哪裡需要找什麼專家,衙門裡的大老爺被稱為「父母官」,爭議雙方往往在泣訴案件詳情後,請求父母官法外施恩,做出情理兼顧的裁斷。
因此,清治臺灣衙門內審案以親自應訊為原則,或是由關係親近者出任「抱告」來代為陳述案情,且常私底下找熟悉衙門事務、與上層關係良好的「訟師」想辦法讓官員施恩。

清治臺灣衙門內審案以親自應訊為原則,且私底下所找的訟師不會出現在公堂上。
如何因應臺灣人根深柢固的傳統觀念?王泰升發現,日本政府沒有在統治初期貫徹「審辯分立」制度,未強制要求委任律師來代理訴訟,反而是遷就清治時期的「抱告」經驗,同意讓爭議雙方的親屬或受雇人擔任訴訟代理人。
而且臺灣人似乎將依法審判下,憑藉法律專業、以法為當事人而辯的律師,視為運用伎倆或關係促使大老爺施恩的「訟師」,故不太在乎律師都是日本人。
一直到日治後期,對於訴訟代理人的要求才逐漸走向法律專業,並有不少臺灣人成為律師。同時臺灣人逐漸明白,法院不是攀關係或求情就能做出有利判決的地方,需要委任專業律師作出有利辯護才有可能勝訴,「審辯分立」的觀念慢慢在臺人心中紮根。
然而,日本畢竟是殖民政權,臺灣人聘用律師大量興訟,這對統治當局沒有好處,反而增加司法資源的開支,故不免視律師為「麻煩製造者」。
因此,在 1919 年的司法改革之前,律師的發展受到不少打壓。在「官司越少越好」這方面,日本殖民當局跟清朝在臺官員倒是立場一致。
日本在臺灣推行的制度,目的不是追求「現代性」,而是為了樹立「日本性」。實現「審辯分立」原則,不如節省司法成本來得重要。
「一國兩制」的刑事訴訟程序
至於決定國家應否行使刑罰權的「刑事訴訟程序」,日治時期的制度沿革就更值得玩味了。日本當局在稱「內地」的本土與「外地」的臺灣大玩「一國兩制」手法,透過殖民地的特別法,來模糊甚至否定刑事訴訟中的「審檢辯分立」原則。
依照嚴格的「審檢辯分立」原則,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律師代表被告為其權益辯護,法官則依法審判被告是否有罪。此制度是西方近代個人主義和自由思潮下的產物,源自人民對國家(審判者)的不信任,與清治時期全權交由賢能父母官定奪的觀念,顯然背道而馳。

依照「審檢辯分立」原則,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律師代表被告為其權益辯護,法官則依法審判被告是否有罪。 圖|研之有物
對於日本當局來說,若要在臺灣落實「審檢辯分立」,一來衝擊既有觀念,容易激起反彈情緒;二來要把懲罰犯罪者的權力,區分出法官和檢察官兩種不同角色,既增加司法運作成本,還稀釋了司法官員的權威,怎麼看都不划算。
因此,殖民地刑事訴訟特別法就在這樣的盤算下應運而生。日治初期,統治者把清治時期輕罪由廳縣衙門直接處斷的傳統,轉化為「犯罪即決制」,也就是由警察官以廳長的名義,對違警罪、課以較輕刑罰之罪,訊問後即做成裁決,導致許多刑事案件的處理上,檢察官連一點角色都沒有。
此外,當時的法院內,檢察官擁有強制處分(如羈押)的權力,法官則有蒐集證據的權力,形同「檢察官的法官化」加上「法官的檢察官化」,讓審檢之間的界線變得極為模糊。
即便在 1919 年司法改革後,犯罪即決的案件減少,但 1924 年與日本內地同步施行新的刑事訴訟法後,檢察官能用書狀取代出庭論告,此舉雖能有效節省司法資源,卻也讓一般民眾幾乎沒有機會接觸並理解「審檢辯分立」原則。
被藏起來的權力分立
最後,是牽涉國家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司法行政分立」。事實上,中國傳統的統治體制根本不存在行政與司法分立,法律規章與執掌刑罰都只是統治事務的一環。「法」通常與「刑」畫上等號,都是施政的工具之一。
三權分立是西方近代發展出的憲政原則,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為了富國強兵而效法西方各種體制,卻對這套「權力分立」觀念有所保留,畢竟要拆解國家統治權,茲事體大。連殖民母國日本自身的政體都不怎麼買帳,更不用說落實於殖民地臺灣了。
日治 50 年,從未實施日本的行政訴訟制度,就是不讓司法部門審查行政機關所為處分。確保行政權的獨大,也減損了臺灣人對「司法行政分立」的認識。
總的來說,王泰升認為,日本殖民政權確實將現代「司法正義觀」帶進臺灣,卻為了緩和制度變革所可能產生的反日情緒、鞏固統治權力、撙節司法資源等各種緣由,並未真正落實各項現代法中的分立原則。
臺灣人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道路雖被開啟,但是制度的不健全讓步履走得相對蹣跚!直到今日可能還有法官、檢察官分不清的情形,或是萬事求總統(大老爺)幫忙而不知權力分立等舊有觀念的遺留。
深入全臺法院的史料蒐集之旅
為了研究日治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王泰升研究團隊爬梳了大量史料,用法律、公文、發言紀錄勾勒出一整個時代的樣貌。另一個更漫長而辛苦的研究方法,就是《日治法院檔案》的蒐集與整編。

日治時期臺中地方法院「判決原本第一冊」,始自「明治貳八年」(1895 年),見證臺灣首度出現當今的司法審判制度。 資料來源|《日治法院檔案》,臺中地院,獨民判決原本第 1 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提供。
1998 年,王泰升以受臺灣高等法院委託,整理原臺灣總督府法院藏書之便,發現若干日治末期民事判決原本、訴訟程序橫跨兩時代的案件、戰後接收卷宗等,進而開啟《日治法院檔案》的拼圖之旅。
他與團隊花了超過十年時間,找到日治時期臺北、新竹、臺中、嘉義等地方法院的民刑事判決原本、公證書類、各類登記簿等司法文書。另有較零星的日治時期高雄、花蓮兩地方法院的民刑事判決原本和登記簿,及澎湖出張所的公證書和登記簿。
團隊將這些年代久遠、數量龐大的珍貴史料,拍成 2,295,000 張的影像檔保存。這還只是研究工作的一小步,接續還要編碼、歸檔並分析資料。每一樁案件都要進行編碼,從日期、案件類型、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特質、訴訟結果等變數,拼湊出當時人民跟法院間的種種關係。
光想就令人頭疼的工作,憑著一股王泰升稱之為「氣」的堅強意志,加上臺大圖書館項潔館長對建立數位資料庫的鼎力相助,這些看不見、摸不著、藏在大腦中的觀念變化過程,才得以躍然紙上。

2002 年,王泰升(右前二)及研究團隊為整編《日治法院檔案》,特別到臺中地方法院庫房履勘、拍攝檔案。 圖|王泰升
放棄高薪律師路 全為了一股「氣」
王泰升是臺灣著名的法律史權威,但當初踏進該研究領域,並不是最初的生涯規畫。
「我去美國原本不是要當學者,是要當律師的。我當時已開始在國際事務所擔任商務律師,『錢』景一片大好,但就是不小心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學術議題,就一頭栽進去了。」
王泰升口中的有趣議題,正是日治時期的法律史。當年的他在臺灣接受七年的法學訓練,對日治時期法律的認識卻是一片空白。
「不是因為我法制史的課全部翹課!」王泰升笑著說:「而是因為那是個諱莫如深的年代,相關資訊在國內根本沒有機會接觸。直到 1989 年去了美國,我才很汗顏地發現,關於臺灣法律的史料,竟然在臺灣看不到,在美國卻唾手可得!」
故鄉的歷史卻必須在異鄉才有辦法發掘,讓王泰升忍不住一股「氣」衝上心頭。臺大法律系雖然沒有教他這段歷史,卻養成了他崇尚多元的價值觀,還有為社會底層發聲的使命感。
「沒有人的歷史該被抹煞,日治時期如此、原住民族歷史亦是如此!」
多虧這股「氣」,我們才得以知曉這段原本近乎空白的歷史。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王泰升為自己的研究下了註腳,也為法學後進指引前進方向:
把法學帶進歷史,可以看見不一樣的歷史。同樣的,把歷史縱深放入法學研究,也可以得到嶄新的法學思維!

王泰升勉勵眾人:把法學帶進歷史,可以看見不一樣的歷史。同樣的,把歷史縱深放入法學研究,也可以得到嶄新的法學思維! 圖|研之有物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請<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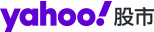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