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鄧家妹子
我和鄧麗君是在台北西門町的夜巴黎歌廳同台演出時結下的善緣。
第一次看見鄧麗君的時候,她看起來就十來歲的樣子。她由媽媽陪著,像一隻輕靈的燕子,經過咖啡廳去樓上的舞廳唱歌。那段日子,我正無所事事地跟著小五哥論道求學,那晚我們正好在東方飯店咖啡廳。
雖然她那時只有14、5歲,已經是很紅的少女歌手了。看到鄧麗君,我像傻瓜一樣目不轉睛地盯著她看,她轉過頭來衝我微微笑一笑,我更懵了,像觸電了一樣,呆若木雞地站在原地很久。正是:六宮粉黛無顏色,回眸一笑倒一地。等後來我跟她熟悉了才發現,原來她對誰都那麼柔情。
吸雞蛋養護嗓子
猶記得每次當司儀宣布她出場的時候,台下的掌聲頓時此起彼伏。歌曲間奏的時候,觀眾會自發地為她打拍子,節奏整齊又響亮。而她一開口,掌聲瞬間停歇,象有個隱形指揮一樣。這是大牌藝人的榮耀,她當時小小年紀已經擁有了。
而我只是個剛出道的新人。在那之前,我都是在一些小歌廳唱歌,薪水不高,觀眾也不多。到了夜巴黎,原以為可以一展自己的才華,誰知道好景不長,才3個月後就不再給我續約了。我和麗君的第一段同事的緣分就這麼短暫。
臨別的時候,重情重義的鄧媽媽和麗君送我走出後台那扇門,鄧媽媽說:「王大哥,有空回來看看我們。」 麗君也走過來接一句:「王大哥,你保重,有空回來看看我們。」 一瞬間我特別感傷。「謝謝謝謝!」 我邊說邊尷尬地左顧右盼,擔心她們看到我忍不住的淚水,想找個她們看不見的方向。
雖然同台時間不長,但這段告別是我永遠難忘的回憶。
鄧家一共5個小孩,4男1女,鄧麗君排行老四,是家裡唯一的千金,父母的掌上明珠。五弟長禧曾說過:「我們家那時候環境不是很好。我媽媽也不知從哪裏聽來的,剛生下來的雞蛋用開水燙一下,兩頭鑽個洞吸來吃對嗓子很好。我們家有一只老母雞,每天剛好只能下一個蛋,那個蛋就由她來獨享。」我始終不知,她後來演唱事業的飛黃騰達,是不是和她家的母雞下蛋有關係。
鄧麗君從小就很聽話。鄧家的家規很嚴,都是鄧爸說了算。即使大哥、二哥、三哥、五弟都已經成了家,爸爸坐的位子還是沒人敢坐,大家看到他,依然就像老鼠見到貓一樣。即使鄧麗君在泰國清邁去世,爸爸仍以北方漢子(河北人)的堅強強忍著悲痛,含悲淡淡地應對。
鄧麗君念中學的時候,在台北金陵女中。金陵女中是個校風嚴謹的教會學校,聽說鄧麗君晚上在歌舞廳演唱,學校認為給聲譽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就叫她做個選擇:要麼繼續念書,要麼離校就業。威嚴的鄧爸認為,憑勞力賺錢,沒什麼見不得人,一怒之下就離校退學了。儘管鄧麗君認為這是她學業上的遺憾,但我認為這是她事業上騰飛的起點。
鄧媽媽也是個冷靜慈愛的母親。因為我們都是山東老鄉,所以她對我都很親切。每次看到鄧媽媽的笑容、聽到她的鄉音,我都感到特別溫暖。
鄧麗君很有家教,溫良謙讓,平時少言寡語非常安靜,但一開口就很幽默。我從來沒聽過她在背後閒嘴他人,你跟她說誰,她都笑一笑。她總是獨來獨往,雲淡風輕。
她很有語言天賦,英文、法文、日文、廣東話、閩南話都很好。享譽亞洲,多次在日本獲得金獎,風靡紅白歌會,出了超過300萬張唱片,很少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地球村的華人社會幾乎都有她的忠實歌迷。
香港唱到東南亞
70年代初我去香港歌劇院長期演出,她剛好就在對面的國際夜總會演出,我和她又喜相逢了。她有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就會翻開報紙,看看夜總會歌廳歌手名單上有沒有熟悉的朋友,我就是這樣在香港被她發現的。
我比她去香港早兩年,算是識途老馬。每到周末的時候,就帶她出去放風。因為麗君特別喜歡騎馬,我就常帶她去沙田馬場學騎馬。她對騎馬很有天賦,膽也大,很快就馬上見功夫了。
我在香港有個要好的朋友叫吳良辰,大家叫他「肥仔」,很會做生意,人好又大方,他鄧麗君同年同月生,經常帶我們出去玩。肥仔對香港「門兒清」,知道哪裏好玩,哪有好吃的。他帶我們去吃沙田乳鴿,到羅浮山吃海鮮。我順便拿著望遠鏡遙望大陸,看大陸老鄉都長什麼樣,後來發現都和我們都長得差不多。那真是一段難忘的青蔥歲月。
後來到了新加坡,我在海燕歌劇院唱歌,麗君到新加坡演出時,又是翻翻報紙就找到了我。我帶她到處去吃大排檔,大排檔有各種各樣的口味,廣東的、福建的、馬來西亞在地的...她對飲食文化很有好奇心,無論五湖四海、異國他鄉的口味都有興趣。
所以每次晚上下了班,我就是她吃宵夜的導遊,因為新馬一帶的小吃大排檔,我已經是個老饕了。她新加坡的經理人叫小管(管偉華),也是她最好的朋友,後來也成了我的經理人。就在前不久,看到新聞說小管走了,我很傷感,老朋友又少了一個。
後來74年我和麗君又一起去越南西貢唐人街麗升歌廳演出。那時她已經是東南亞的紅牌歌星,每天賺400美金,而我每天只賺100美金,既要主持還要唱歌。不過400美金對她來說沒啥感覺,而100美金對我已經是個非常得意的數字了。
我們在越南一演就是一個月。她和鄧媽媽住在新開張的天虹酒店,我住在對面的老酒店八達。每天演出完畢,我們都一同在酒店附近的越南小吃吃宵夜。剛到越南的時候,半夜常常驚恐得睡不著覺,尤其是烽火三月,晚上睡覺都聽得到遠方越共遊擊隊的炮火聲和警車鳴笛聲。不過數度進出越南,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一直到越南解放後。
這一路走來,我和麗君一段緣接一段緣。鄧媽媽很喜歡我,第一因為我們都是山東老鄉。第二我當年一心一意掙錢給家裡還債,或許令鄧媽媽有點感動。再加上見到窮兇惡煞的人我還有點膽識,所以可能她們和我一起也多少有些安全感。
1978年是我人生最挫敗的時候,差點就被台灣三家電視台聯合起來給「默契」掉了。而麗君那時候的影響力已經譽滿港台、遠播大陸,大陸盛傳「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於是,台灣當局給麗君舉辦了一台盛大的晚會,叫《君在前哨》,規模之大、收視之廣,前所未有,後無來者。我沒想到的是,麗君竟然點名邀請我去做她唯一的嘉賓主持。
對於麗君的這個要求,晚會的承辦方三家電視台是有意見的。台視總經理石永貴說:「鄧小姐的晚會遇到了一點麻煩,她邀請的這個嘉賓主持凌峰,是被三台默契掉的,三台反對他參與。」石總難以定奪,只好打電話請示晚會的最高領導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王將軍說:「凌峰是誰?這是鄧麗君的晚會,當然要尊重鄧小姐的意見了!」這段插曲是多年後,有一次過年,石總給我揭開的祕密。我沒想到我這個小人物的上台問題,已經上升到官方這麼高的層級。
謝麗君再造之恩
《君在前哨》的演出, 我說了段脫口秀,唱了首〈船歌〉,果然一炮而紅。石永貴總經理看了演出很興奮,我一下台,他就跑到後台來了,遞了張名片:「我是新來的台視總經理,希望你到台視來,咱們聊聊。」
自此後,我有了自己在台視的節目《鬱金香》,後來又做《電視街》,好運一個接一個來。
麗君那些年長時間在海外旅行演出,但每次回台灣,我們都會小聚一下,一起去吃山西館,來碗刀削麵、貓耳朵。她始終是我唯一的最重要的後盾。所以說,我能有今天,麗君對我有再造之恩,台視總經理石永貴亦是我演藝事業的貴人。
成名後的鄧麗君身邊不乏男人,但同齡的配不上,配得上的有家室。鄧媽媽寸步不離地守護,連公蚊子都不敢靠近。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在台中,《君在前哨》演唱中場休息時,她慎重的領來一個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公子,給我介紹是她的男朋友。
他不擅國語,他們倆英語粵語相談甚歡,我後來知道他是新加坡亞洲糖王之子郭孔丞。可惜這段戀情無疾而終。或許因此,麗君很傷感,那段日子報章雜誌有一些她情感上的緋聞。
84年,我在拉斯維加斯劇場做秀,她打電話來,本來是和我商量《十億個掌聲》演出的事。我出於關心,上來就脫口而出:「你最近要注意自己的行為啊,報紙上的負面新聞對你不利啊!」電話那頭沉默了,她嗯地應了我幾聲,就放下了電話。我忙著演秀,沒心沒肝的。過了長時候才醒悟過來,上次演出的事怎麼沒下文了?這才醒悟,自己說話太直接,自視麗君的大哥,忘記她已經成年,帶著老大哥的口氣信口開河,關懷過度了。
再後來我去大陸拍八千里路,我們倆聚少離多。93年底,麗君的五弟兼經理人長禧首度造訪我們北京亞運村的家,讓我約著九洲文化的總經理遲晨曦,一起商量關於麗君回大陸探親及演出的破冰之旅。
十億掌聲夢成空
我們初步商定大陸之行先赴西安探訪姑姑,再酌情決定是否返鄉河北大明府或是回山東鄧媽媽老家省親,順道造訪北京上海了解破冰演出的可能性,以備來年唱響「十億個掌聲」之原鄉圓夢。另則,長禧亦代表姐姐表達心願:希望九洲能保証此行探親之旅在新聞上「不被曝光」。九洲欣然同意,又委婉提出:能否請鄧小姐在行前,為兩岸合作之盛會創造點「氛圍」以表誠意?
老五回香港給姊姊匯報,麗君難掩激動,她早就盼望回大陸演出了,還催促老五早點到香港新華社辦理簽證,以備隨時北上破冰。我們商量了一個給大陸之行創造氛圍的方法:香港每年有六四的燭光晚會,以往都會邀請鄧麗君參加。但是94年,老五安排麗君早早地去法國錄音,麗君人不在香港,也就沒法成為燭光晚會的頭條了。對於這項安排,大陸邀請單位一直表達感謝之情。
可遺憾的是,95年,大陸之行還沒如願,麗君就在泰國清邁突發哮喘去世。「月圓的美,是世俗的美,月缺的美,是詩化的缺,憾的揪人心!」麗君已化作彩雲飄然而去,她留在人間的十億個掌聲十億個夢,已成為一個美好卻再也圓不了的夢!
有一段時間我不相信麗君走了,後來慢慢調整過來。所謂過化留神,從好的方面想,這樣的離去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她的美好成為一種定格,在所有人的記憶裡,永遠是最美的樣子。
這些年,我為療養移居泰國清邁,將這視為我養老的第二故鄉。或許冥冥之中,我與鄧家妹子的緣分未盡,情誼未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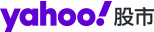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