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正在被疫情邊緣化
從我有記憶以來,銀行就是一個高大上的代表,從台灣早期的三商銀到現在一棟棟林立在信義商圈的金控大樓,它們代表的不只是台灣金融的頂梁柱,更應該是產業推進的助力器。但時至今日,這些無數莘莘學子曾經懷抱夢想踏進的金融帝國,不但在疫情肆虐之際離資本市場越來越遠,更在有形的手步步進逼之下漸趨邊緣化。事實上,將直接金融讓位給政府紓困及央行印鈔根本怨不得旁人,既得利益者從來都很難革自己的命。它不但將越來越難提供養分給年輕的金融幼苗成長,還可能在疫情過後的新產業發展浪潮裡缺位。
曾幾何時,大多數國家的銀行一直主導著對家庭生計和企業發展的放貸。連資本市場最發達的美國,銀行也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John Pierpont Morgan就是美國在1880年代鐵路發展背後的有力支持;接著美國更憑藉著花旗銀行的全球化,支撐了美國企業的海外擴張;而其資本市場的直接金融更是踩著商業銀行的肩膀才為美國塑造出了無與倫比的金融強權。這所有一切都成為了今天美國「聯準會」(FED)在應對一波波經濟危機時能夠發揮巨大影響力的背後原因。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銀行的定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在1933年到1999年的法律規定,商業銀行是必須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但2000年後的混業經營開始主導了美國的資本市場,這些金融機構開始露出了貪婪的本性,他們靠著其資產儲備的一小部分盡力槓桿,並且通過短期借款來提供他們的長期貸款或持有長期的投資證券來獲利,那讓他們一再暴露在風險之中,終於讓自己在經濟歷史上醜聞纏身,更在2007~09年的金融危機時為自己烙下了不值得信賴的醜陋標記。
在緊接而來的法遵一層層限制下,不只銀行,所有的傳統金融都變得更加避險,其中大多數都轉身成了大型金控的一部分。而且,由於資本市場的新一波創新改變了證券交易和債務的發行,並導致非金融機構可以提供更多的直接貸款,更讓它們處於了相對落後的地位。其結果就是銀行的企業貸款在GDP的比重難以突破,只能勉強維繫住既有客戶的放貸額度,更重要的是由於產業調研能力的不足,它們在新時代的放貸熱潮中注定無法再參與其中。銀行的停滯和風險規避進一步讓央行在應對疫情時有了更大的施力空間,各國央行終於不再成為銀行的最後貸款人,而是直接成了整個市場的做市商。
這一切還讓精通科技的非銀行機構逐步崛起,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Richard Berner就認為對銀行的嚴加監管是讓非銀行體系在監管套利空間中找到發展機會的主要原因,但金融科技更促進了整個金融運作的轉變,特別是在過去10年,它讓移動支付迅速增長,也讓銀行體系外的直接金融活動越來越活躍。自2012年以來,企業增加的債務存量中,銀行借出的債務僅增加了GDP的2個百分點,非銀行部門持有的股權債務則上升了6個百分點。一組監管機構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的數據顯示,2007年全球非銀行金融資產為100兆,相當於GDP的172%和總金融資產的46%,但如今這些資產總價值已變為183兆美元,占GDP的212%,占全球金融資產的49%。
私募股權PE也扮演著重要的推波助瀾角色,全球最大的五家PE公司(Apollo、Ares、Blackstone、Carlyle以及KKR)管理的資金中至少有1/5投資了信貸資產。自2010年以來,這些PE籌集的2600億美元中,更有高達2221億美元用於信貸投資。整體而言,非銀行金融機構已經積累了價值8120億美元的信貸資產,從規模上講,這已經相當於未償還企業債券的14%。FED這次更是理所當然地繞過了傳統金融機構,直接介入了資本市場的運作,正如國際清算銀行在其最近的年度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各國央行巨大而有力的流動性支持遏制了市場的失靈,但它也催生了充滿風險的金融資產價格,並影響了未來的風險市場定價。銀行的停滯或許不是一個壞事,但它已經注定淪為疫情過後的金融發展旁觀者,當大量活動在看不見的陰影進行時,銀行只能被動地在黑暗中摸索著自己看不見的風險而走向邊緣化。
(作者為創投合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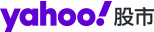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