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淬煉的流金歲月

我從來沒有想過寫「回憶錄」這檔子事。
我出身高雄地方公務員之子,成長環境單純,自覺不善於察顏觀色,並不適合宦途,沒想到後來會進入政府任職。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也不算是意料之外。幸賴長官與同事們的協助,方使我這個愣頭傻鳥,在不同的崗位上幸不辱命,先後完成國家交付的任務。
先父趙公淑訓為人內斂寡言,我幼承庭訓,也養成低調的人格。後來承乏外交工作,不能再「沉默是金」,反而到處為國宣勤,是想像不到的轉折。雖然創造了若干成績,足堪告慰長官,但後來被迫提前離開畢生奉獻的外交志業,轉戰金融圈,而且涉足兩岸交流;其後又跨足航空服務業,擔負若干社團工作……多年來的淬煉與起伏,真讓一個「南台灣北漂(甚至外漂)」的戇囝仔體驗到—人生如戲、而且劇本隨時在變!
我棄公從商後羈居海外期間,偶而回國,會盡量抽空去看老長官錢復先生。大概是2015年夏天,他跟我聊到外交部某某前輩出了回憶錄,說著說著突然表示:「Leonard(我的英文名字),你應該寫點東西。」我當即謙辭覆稱:「寫回憶錄我不敢當。第一,我還不覺得老;第二,我沒那麼有名,不敢貽笑大方。」
他聞言後正色道:「這跟老與名氣沒有關係。台灣年輕一代目前接受的訊息多元無章,大多為Secondary sources(二手資料)。你應該趁著還有記憶的時候,把一生經歷整理一下,讓年輕讀者們有個Primary sources(原始資料)。」
這一番話讓我無言以對。2015年底,我回台擔任中信金控台灣人壽常務顧問,無行政責任牽絆,較有餘裕時間,遂開始整理以往的公務資料及個人思緒,將之逐漸形成文字。白天執筆以後,夜晚裡沉緬往事,回顧所經歷的人事滄桑與世局紛擾,難以成眠。就像看懷舊老電影一樣,畫面雖然斑駁,劇情卻鮮活無比,全都跳到了眼前。
既然渥蒙期許為「Primary sources」,我臨深履薄,敘事的內容方面必須求「真」、以誠為重,不敢譁眾取寵或誇大不實。另外為了避免困擾,我文中絕不批評他人;如果必須臧否人物,則多從光明面出發,希能闡揚社會的正能量。只有在敘述少數重要事件時,因導源於人為因素,不得不還原全貌,但多為就事論事,絕不借題發揮。
本書內容不敢自詡為「回憶錄」,僅在追述一個外交工作者為國打拚的浮光掠影。猶記國小課本上讀到晏嬰與藺相如等偉大壯烈事跡,心儀不止,當下決定未來要做個為國家旋乾轉坤、化危為安的外交官。其後中學時期興趣改變,沉迷於西洋繪畫;大學主修法律,卻嚮往新聞工作……在經歷一連串「用情不專」的啟蒙歲月後,我最後還是回歸到原本「初心」,在1978年加入了國家的外交行列。
環顧古今中外,中華民國外交處境的困頓,可謂獨一無二。其中原因很多,有涉及國際環境演變者、有涉及國家主政者政策方向者、有涉及國際盟友態度轉變者、當然也有涉及國際對手實力消長者。無論如何,國際賽局也是「成王敗寇」,不幸的結果既已成為事實,追究原因或前人責任已無補於事,只有由後繼者設法「挽狂瀾於既倒」;尤其重要的是—可千萬別再「重蹈前人的錯誤」了!
基於這種「台灣的外交既然『先天不良』,就不能再『後天失調』」的自我期許,我在工作崗位上,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希冀能將一手「壞牌」打成「好牌」。這也是本書書名的起源。
當年我首次踏進凱達格蘭大道(當時稱為介壽路)上的外交部正門時,凝視門上「外交部」三個銅鑄大字,腦海裡浮現著「巴黎和會」、「開羅會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退出聯合國」等近代史上影響台灣的正反外交事件。激動之下,我浪漫且悲壯地自我期許:一定要為多難的中華民國外交,做出一點貢獻!
進入外交界以後,我先後承乏華府對美政府與國會之聯繫、加拿大的開館、與非洲史瓦濟蘭(現已改名為史瓦帝尼)的「草根外交」等工作。秉持著「言必信、行必果」的待人處事原則,及勤能補拙的精神,加上長官的支持與同事們的協助,幸能無愧職守,完成各階段的任務。其中值得回味者,例如:在美國創下「台灣三等祕書可見到美國國務院副助卿」的空前紀錄;說服加拿大政府給我駐加人員外交待遇,創下G-7 國家首例;及與史國國王結成好友,迄今他仍然守著台灣,是我們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國……。當然,此期間我要特別感念蔣孝嚴、錢復、連戰、陳錫蕃等先後師事的長官,以及他們對我的指導與鞭策。
外交生涯過程中,我應大學同窗陳水扁前總統邀請,於2001年初轉至總統府服務,任滿後外放非洲,繼續外交本業。我雖然一本為國服務的常任文官立場,處理公務上超越黨派,但也不免被捲入台灣「藍綠之爭」。2009年自非洲回國後橫遭政治獵巫,空有「大使回部辦事」名義,套句時下流行語彙—「被休息」了。然而在外交部無事可辦期間,沉潛自省、大學兼課,亦非無所得。
2010年高中同學某商界友人拜會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邀我同往。當會見久違的老長官,不知如何啟齒之際,該同學在旁好意地首先發言:「當年趙麟一時不慎,進總統府幫民進黨做事,請主席原諒……」不料他還沒講完,連氏立刻打斷表示:「趙麟不是幫哪一黨做事,他是幫國家做事。有兩件事是沒有黨派之分的,一是外交,一是國防……」
聽到此處,我積鬱了一年多的委屈,彷彿遇到知己的空谷梵音一般,瞬間獲得療癒與滌濯。淚眼中聽完他這一段話,鼓舞了我繼續向前努力的決心。
2011年衛生署邱文達署長邀我借調該署,協辦國際醫療。我不計較高階低用,仍願為政府效力;不料再度遭到行政院高層駁回,原因仍然是—「政黨顏色不對」!
至此,我不禁想起昔日中國大陸傷痕文學劇本《苦戀》中的一句話:「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
眼見國家已被當時執政黨強分異己,我孤臣效力無處,2012年12月,提前向外交部請辭,轉入民間金融界。在暮秋的蕭瑟涼風中,我走出外交部的大門,望著同樣「外交部」三個銅字,回顧從前,心中無限感慨。雖然「美好的一仗已經打過」,我俯仰無愧,但總有「這仗還未打完」的一絲遺憾。
本文轉載自《把一手壞牌打好》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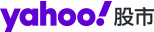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