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詩選-我若不是荒野,就是一個夢
中國時報【陳仁華】 欒樹下走過,就是一生了。 陽光灑進來了,中斷了肉身的夢,開啟了影子的白日夢。 直到分開之後,我們才又相聚了。 我曾這樣熱鬧生活,當寂寞認不出寂寞時。 跑起來,我就是荒野了。 順著我吐出的絲,我到了我不在的地方。 你再怎麼追趕,也追不上、趕不及你的遲到。 人是遲到的動物,人遲到於當下、遲到於自己,因而有了記憶,有了意識。 對於人類這種習於遲到的生物而言,當下的存在,從不存在。 地上的我,遲到了一秒,天上的孤星,遲到了一億年,我們因而得以相遇。 我的死亡早到了,以遲到為天性的我,永遠不知道我死了。 每一棵路邊小草都在提醒文明:這裡,始終是荒野。 星空,頭頂上的荒野。 走入你自己,你需要光速的凝然,像一棵樹,把光留在身上。 去掉詞語的呼吸,去掉呼吸的詞語,交談得起來嗎。 遲到的消息說「你死了」,但收信者早已輪迴到下一世,一隻剛喝完下午茶而在咕咕叫的野鴿子。 在上帝的點名簿上,人缺席於自己。 今天,不是早到為明天,就是遲到為昨天,今天從沒準時抵達為今天。 跟著一隻狗一直找下去,你總會找到阿茲海默症的故鄉。 失眠咀嚼著我,吞也不是,吐也不是。 跑完步後,讀一首詩,每個字都在替你呼吸。 就只因我把你的不在當作在,他們就決定叫我為「智人」。 他們發現一根手指,在阿拉伯半島,八萬六千年前,一根曾把不在摸成在的手指,而今,這根手指的後裔,我們,把在摸成了不在。 樹脂,裹住了地球的一次心跳。 醒來,看見一個夢堅持不肯謝幕,在枝頭上。 貓當下於貓,人遲到於人。 我比靈魂早到人世一億年,我比影子晚到人世一秒鐘,我是肉身。 當我跑步時,我喜歡我是一個移動的荒野。 一棵春天的樹,成千上萬片嫩葉,對著新月,睜開成千上萬隻眼,見證了貓的轉世。 當換氣聲與腳步聲交歡,一個跑者就誕生了。 牆聽著路過男女的山盟海誓,牆忍著,牆不笑。 在少男少女的彼此追逐中,興奮的是空氣。 像愈活愈不知所云的殘簡那樣活著,我。 終於,蒸汽火車頭駛出子宮,穿越人肉隧道,準時抵達某人的命盤。 我若不是荒野,就是一個夢。 詩,當然可以走入故事,但結尾處,總是走出故事,走向荒野。 在遺忘記憶之前,我們早已遺忘了遺忘,由於遺忘了遺忘,我們於是以為自己記得了些什麼。 欲望渴求的,不是滿足,而是滿足的推遲,欲望是推遲的平方。 誰當下滿足著自己,誰就是荒野,蝴蝶蘭是,貓也是。 在我們發呆的時候,誰在替我們發呆? 在妻子跟我鬧彆扭的時候,我就會想到:我只能愛你的背影嗎?我只能愛我的陰影嗎? 因為吃了伊甸園產的蘋果,人總是把此在活成彼在,把不在當成在。 我們推開了所有的當下,我們創造了時間流動的假象。 適合所有人的墓誌銘:直到入土的那一天,我還是沒成為我自己。 牽著手,就是橋了。 遲到的是影子,輪迴的是影子,肉身,當下,成佛。 跑完步後,把心跳藏在石頭中,跑完步後,只為野鴿的咕咕聲心動。 波羅的海很近,我的海很遠,遠到我從沒涉足過,遠到我注定要溺斃於別人的海。 荒野中,影子問候著生,問候著死,文明中,影子不讓你生,不讓你死,只讓你輪迴。 野貓喵了一句,牆聽懂了,牆中的竊聽器聽不懂。 在流浪的年代,語言與風曾是同一語系。 牆圍住了語言,牆把語言圍成文字,最好的文字,也只能哭牆。 每個人每天都在寫自己的百科全書,寫到了最後一天最後一頁的最後一句,闔上書後,總要丟下一句:那不是我。 失語的詞,連呻吟都不會了。 上帝給了她一個又一個禮物,但她一個也沒打開,只因周圍擠滿了嫉妒的眼神。 突然伸出的兩隻手,從我的背後,蒙住我的雙眼,說:猜,你是誰。 而風,在體內打瞌睡,在豹眼睜開前。 每一個不想失語的詞,都擺出了告別自己的姿態。 在烏臼與我共飲下午茶時,樹長出了一樹的人心,人長出了一身的樹皮。 沒有讀者的寫作,甚至不給自己看的寫作,天邊一朵雲的塗抹。 也或許,我唯一想說的那一句,自殺了。 像蝴蝶的蜻蜓,像蜻蜓的蝴蝶,像愛的恨,像恨的愛,像生的死,像死的生。 跑著,跑著,抖落了一身的字與詞,渾身只剩風的交歡。 塞凡提斯任堂吉訶德不朽,堂吉訶德任塞凡提斯腐朽。 人讓上帝失業,人工智慧讓人失業。 在兩棵樹之間,在木訥與木訥之間,完成了最神祕的溝通。 人人都在排隊,等著領取配額的孤獨。 水開了,世界有了目的,為了變成一朵雲。 一朵雲來了,為了把一個人變成一個薩滿,在華爾街上。 我們都是轉世專家,光是一趟跑步下來,都可以轉世個好幾次。 你殺不死影子,影子可以殺死你。 詞語自己走進筆記本,為了發酵,為了釀出被記住也被遺忘的酒。 習慣遲到的我,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死了,而蝴蝶蘭開著,沉香木綠著,迷了路的蚊子迷路著,彷彿在為死者唱著引路的度亡經。 煉金術士至死不悟:他的呼吸已經是煉金術。 遺忘遺忘著遺忘,這就是記憶的通關密語。 在忘牆的兩側,睡著你和你從未謀面的自己。 即身成佛,最容易,但對人卻是最難,就只因人即不了身。 你親過自己嗎? 風吹過水面,那波紋就是我。 自殺者還是沒殺死鏡子裡的自己。 我有鑰匙了,但,門在哪裡呢? 賈寶玉是石頭的一個夢。 讓影子跟肉身一起腐朽,這就是功課。 我來,為了埋葬我的影子。 淋浴時,仰著臉,水沖掉了臉上的臉,臉下的臉哭泣著。 等著溫暖的手來撫摸的野貓,等到的卻是逐漸冷卻的引擎蓋。 瞎了,因為眼中擠滿了影子。 一旦曾變身為風,你再也不想成為別的什麼了。 我伸出的手指,何曾觸摸到你?我最初摸到的是喧囂,最終是孤獨。 林中鹿不需要林中路。 荒野中不需要椅子了,你不是站著的一棵樹,就是倒下的一棵樹,荒野中不需要椅子了。 耶穌的沙畫,耶穌也不懂。 你會需要的,我的歌,沒有歌詞,只有節奏,當你不知為了什麼而呼吸時,你就唱對了。 天上掉下來的句子,雨水沖走的句子,我都喜歡。 吹了整天的海風,文字,像岸邊山坡上的野百合,沒有感想,只剩感性。 為了追求簡單,把自己搞複雜了。 消失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消失。 呼吸得夠深、夠孤獨,直到你壓倒孤獨,直到你比孤獨更孤獨。 我的第一次出生是通過陰道,第二次出生是通過跑道。 跑步,只是為了讓自己慢下來,直到跑入石頭之中。 你被河流襲擊過嗎?從腳背到腳踝、小腿、大腿、腰…,那時真正嚇到你的是:你就是一條河流。 永遠找不到門,只因你就是門了。 真實,是可重複的一切,還是不可重複的一切?科學(文明)沒有任何根據地選擇了前者。 影子死了,又在肉身上撒了一泡尿,犯規的靈魂就這樣又被丟回到了人間。 詩打噴嚏,噴出來的,就是我了。 風吻了這裡,這裡留不住這個吻。 詞失語時,呼吸還在,而不遠處,一直凝視著你的那隻黑豹,聽懂了你的呼吸。 注定要一再、一直錯過的此岸,就成了彼岸。 你的背揹起了你的影子、你的命運。 合十的手指間,湧動著,海潮之聲。 一顆沙子裡頭的心跳聲,聽見了嗎? 影子和詞語決鬥,倒地的是肉身,看戲的是呼吸。 明明渴望著重量,影子卻繼續減肥著。 跑步,為了擺脫影子,跑步,都是跑向肉身、跑向荒野。 如果沒有貓的話,我們會活在怎樣一種愛的困境中:影子如何擁抱影子? 我在波赫士的一句詩下,畫了一道灰線,我改變了波赫士。 詩句推敲著,該不該讓我存在。 蛙鳴聲聲忘卻自己是蛙鳴,如誦金剛經聲。 你不用忘記這一切,這一切早已忘記你,就在你最輝煌顯赫的時候。 在這裡錯過這裡,所以在這裡想念這裡。 我甚至忘了我到底忘了什麼,在一陣清風拂面的時候。 我們儘可以互相追逐,我們絕不可以在一起,我們是忠實的愛情信徒。 天空凝視著池水時,池水打了個嗝,那就是我了。 阿姆斯壯登月的那一步,還是踏在荒野中。 我厭倦了我的厭倦,我說不上來我的說不上來。 摸摸我吧,如果你不是影子,我也不是影子,摸摸我吧,就像一棵低垂的行道樹摸了行人的頭那樣。 如果人天生有三隻手的話,他就不會做二元思考,而是三極思維,接著,請再想像一下千手觀音,祂的思考會是怎麼一回事。 從鏡子中,伸出了一隻手,摸著我的臉:啊,這就是我始終搞不懂的一切。 筷子在飯裡翻尋著飢餓。 一壺水,把前世煮成了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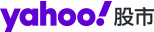
 Yahoo奇摩財經
Yahoo奇摩財經 